翻译学丛——钱春绮:一个人的翻译
钱春绮(1921―)江苏泰州人。1946年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后长期行医,60年代转而从事外国文学翻译活动。历任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德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上海翻译家协会名誉理事和上海文史馆名誉研究员。翻译出版有席勒、海涅、歌德、尼采诗集及波德莱尔等法国象征派诗人诗集多种。
85岁的钱春绮先生精通英法德日俄5门外语,此外在西班牙文、希腊文、拉丁文上也曾下过大力气。翻译是钱先生一生的爱好,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自由撰稿人生涯的他开玩笑说自己失业三十余年,除稿费外从未有过其他收入。但他却嚼饭哺人,为国人奉献了那么多精神食粮。这是百余年前歌德、席勒、尼采诸人的幸运,也是中国几代外国文学读者的幸运
钱春绮先生今年85岁了,和体弱多病的老伴住在上海西北郊的一套两居室内。房间不算小,但堆了很多东西,感觉气氛有点凌乱。钱先生育有两女一子,儿子远在美国,小女儿定居香港,都不在身边。大女儿在同城的另一头,平时往来也很寥寥。谈起日常起居,钱先生挺乐观,“我有老伴嘛,老伴身体不好,我自己照顾自己也行。”
50年代译诗得稿费8000
钱先生是国内不多的在世德语文学翻译前辈之一,译有德法著名诗人作品多种。作为翻译家的钱先生名满天下,但他做翻译却是半路出身。钱先生一生行止以上世纪60年代为分水岭,分属医生和翻译两个角色,而以翻译达到自己人生成就的顶峰。
对于这一人生转折,钱先生自己的解释颇具戏剧性。他说自己是五官科医生,60年代转单位时想转入皮肤科,却因人事纠葛而未能实现。生性崇尚自由、不愿受拘束的他干脆辞职,挂冠而去转而做起了专职翻译。其实钱先生搞翻译早在50年代就已经开始,据钱先生回忆,1952年他翻译出版海涅诗集时曾拿到8000元稿费,而当时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不过几十元。同时期他还著有医学书籍多种,如《中耳炎》、《小儿脑膜炎》和《组织疗法》等。
但“文革”十年,图书出版业陷入了低潮,钱先生也无书可译,境况颇为困窘。“文革”结束后,译事复兴,钱先生才得以复出。可时过境迁,90年代后稿费制度和图书出版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自由撰稿人的处境越来越难。“我也是靠积蓄生活,自由职业,没法维持生存的啊。”钱先生对此感触良深。钱先生也是在1995年加入上海文史馆后,情况才稍稍稳定,现在一个月能拿到1600元工资。但被钱先生戏称为“翰林院”的文史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的”。
喜欢拜伦,因为“他有激情”
钱先生对翻译用力之勤、体会之深都反映在他书房里堆着的那几十本大大小小的泛黄词典上了。现在他书房中的书远非他藏书的全部,“文革”中钱先生被抄走的藏书就有十几车之多。钱先生精通英法德日俄5门外语,此外在西班牙文、希腊文、拉丁文上也曾下过大力气。他翻译时经常参照不同语种译本,这为他解决疑难问题提供了很大便利。“比如翻译歌德的《浮士德》,基本上参照英译本、日译本也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钱先生的外文词典都是他从解放前一直收藏过来的,据他说直到解放初期,因为很多外国人回国前大量抛售原文藏书,外文书还是很好找。后来就少多了,不过改革开放后,心细的他还是在外文书店买到过旧版的席勒全集。
译道艰深,钱春绮穷尽毕生精力致力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引进,谈起翻译自有一番自己的甘苦体会。举例来说,文学作品中涉及宗教体制用语处常遭误译,如人所熟知的《巴黎圣母院》其实应该译成“圣母堂”,因为天主教汉语词汇里“不存在圣母院,只有圣母堂”。而一般所谓“做弥撒”也有问题,因为只有牧师才“做弥撒”,普通教众该称“望弥撒”,等等。
钱春绮先生从小喜爱文学,至今写诗不辍,积累有大量未刊诗稿,经过“文革”及搬家“洗礼”尚余5到6本,其中长诗2部,十四行诗2部(各100首)。“写诗是自己的事”,除了初中在《大公报》发表过几首诗作外,其他诗他从未发表。钱先生写诗锤炼文思是次,主要目的在于排遣胸臆,浇心中之块垒。翻开这些泛黄的笔记本,大部分诗都标有写作日期,从50年代到90年代不一而足。这些诗题材广泛,有对时代风云的感慨,对长逝亲人的追念、对老友的牵挂,也有寓意深远的咏物诗,如一首名为《墨鱼》的短诗:“你有满肚子的墨水/却写不出一首好诗/你只会把清水搅浑/搅得一团乌烟瘴气。”
问钱先生喜欢外国哪些诗人,他想了半天肯定地说是拜伦,“因为他有激情”。钱先生还说歌德不如海涅有激情,波德莱尔的诗用词简单,马拉美的就不好懂。中国古典文学中他喜欢李后主,近代的喜欢苏曼殊,“他们的作品自然,一看就懂”。对于如何提高翻译水平,钱先生也认为多读多写是唯一途径,“不懂的要多查多问”。
旧雨渐去不坠用功之心
如今钱先生年事已高,已很少出门。但他对时事并不隔膜,对文化界、出版界的动态都很了解。钱先生向记者打听一些翻译同行的消息,还和我谈起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的情况,说她的作品涉及变态心理学,很不好读。这很是令人吃惊。
钱先生是寂寞的。他有一本经常摩挲手边的书――《上海作家辞典》。书是1994年出版的,十余年过去了,钱先生的许多老友相继离世,作家协会也寄来了重新修订此书的通知。书的最后一页上写满了钱先生抄录的这两年文化人士的离世信息,包括名字、去世时间和缘由等。远的如“钱钟书,1998年12月19日,北京,88岁”、“韦君宜,2002年1月26日逝于北京协和医院,84岁,脑溢血”。去年离世的有:“启功,2005年6月30日,93岁”、“梅邵武,2005年9月28日,77岁”、“巴金,2005 年10 月17 日,101 岁”等。
不过,旧雨渐去,并未让钱先生心生怨嗟之意。他仍日日用功,读书写作。目前他正在翻译德国著名诗人荷尔德林的诗歌,已进行到一百多首。钱春绮先生说:“年纪大了,但还希望多译一点。”翻译是钱先生一生的爱好,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自由撰稿人生涯的他开玩笑说自己失业三十余年,除稿费外从未有过其他收入。但他却嚼饭哺人,为国人奉献了那么多精神食粮。这是百余年前歌德、席勒、尼采诸人的幸运,也是中国几代外国文学读者的幸运。
85岁的钱春绮先生精通英法德日俄5门外语,此外在西班牙文、希腊文、拉丁文上也曾下过大力气。翻译是钱先生一生的爱好,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自由撰稿人生涯的他开玩笑说自己失业三十余年,除稿费外从未有过其他收入。但他却嚼饭哺人,为国人奉献了那么多精神食粮。这是百余年前歌德、席勒、尼采诸人的幸运,也是中国几代外国文学读者的幸运
钱春绮先生今年85岁了,和体弱多病的老伴住在上海西北郊的一套两居室内。房间不算小,但堆了很多东西,感觉气氛有点凌乱。钱先生育有两女一子,儿子远在美国,小女儿定居香港,都不在身边。大女儿在同城的另一头,平时往来也很寥寥。谈起日常起居,钱先生挺乐观,“我有老伴嘛,老伴身体不好,我自己照顾自己也行。”
50年代译诗得稿费8000
钱先生是国内不多的在世德语文学翻译前辈之一,译有德法著名诗人作品多种。作为翻译家的钱先生名满天下,但他做翻译却是半路出身。钱先生一生行止以上世纪60年代为分水岭,分属医生和翻译两个角色,而以翻译达到自己人生成就的顶峰。
对于这一人生转折,钱先生自己的解释颇具戏剧性。他说自己是五官科医生,60年代转单位时想转入皮肤科,却因人事纠葛而未能实现。生性崇尚自由、不愿受拘束的他干脆辞职,挂冠而去转而做起了专职翻译。其实钱先生搞翻译早在50年代就已经开始,据钱先生回忆,1952年他翻译出版海涅诗集时曾拿到8000元稿费,而当时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不过几十元。同时期他还著有医学书籍多种,如《中耳炎》、《小儿脑膜炎》和《组织疗法》等。
但“文革”十年,图书出版业陷入了低潮,钱先生也无书可译,境况颇为困窘。“文革”结束后,译事复兴,钱先生才得以复出。可时过境迁,90年代后稿费制度和图书出版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自由撰稿人的处境越来越难。“我也是靠积蓄生活,自由职业,没法维持生存的啊。”钱先生对此感触良深。钱先生也是在1995年加入上海文史馆后,情况才稍稍稳定,现在一个月能拿到1600元工资。但被钱先生戏称为“翰林院”的文史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的”。
喜欢拜伦,因为“他有激情”
钱先生对翻译用力之勤、体会之深都反映在他书房里堆着的那几十本大大小小的泛黄词典上了。现在他书房中的书远非他藏书的全部,“文革”中钱先生被抄走的藏书就有十几车之多。钱先生精通英法德日俄5门外语,此外在西班牙文、希腊文、拉丁文上也曾下过大力气。他翻译时经常参照不同语种译本,这为他解决疑难问题提供了很大便利。“比如翻译歌德的《浮士德》,基本上参照英译本、日译本也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钱先生的外文词典都是他从解放前一直收藏过来的,据他说直到解放初期,因为很多外国人回国前大量抛售原文藏书,外文书还是很好找。后来就少多了,不过改革开放后,心细的他还是在外文书店买到过旧版的席勒全集。
译道艰深,钱春绮穷尽毕生精力致力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引进,谈起翻译自有一番自己的甘苦体会。举例来说,文学作品中涉及宗教体制用语处常遭误译,如人所熟知的《巴黎圣母院》其实应该译成“圣母堂”,因为天主教汉语词汇里“不存在圣母院,只有圣母堂”。而一般所谓“做弥撒”也有问题,因为只有牧师才“做弥撒”,普通教众该称“望弥撒”,等等。
钱春绮先生从小喜爱文学,至今写诗不辍,积累有大量未刊诗稿,经过“文革”及搬家“洗礼”尚余5到6本,其中长诗2部,十四行诗2部(各100首)。“写诗是自己的事”,除了初中在《大公报》发表过几首诗作外,其他诗他从未发表。钱先生写诗锤炼文思是次,主要目的在于排遣胸臆,浇心中之块垒。翻开这些泛黄的笔记本,大部分诗都标有写作日期,从50年代到90年代不一而足。这些诗题材广泛,有对时代风云的感慨,对长逝亲人的追念、对老友的牵挂,也有寓意深远的咏物诗,如一首名为《墨鱼》的短诗:“你有满肚子的墨水/却写不出一首好诗/你只会把清水搅浑/搅得一团乌烟瘴气。”
问钱先生喜欢外国哪些诗人,他想了半天肯定地说是拜伦,“因为他有激情”。钱先生还说歌德不如海涅有激情,波德莱尔的诗用词简单,马拉美的就不好懂。中国古典文学中他喜欢李后主,近代的喜欢苏曼殊,“他们的作品自然,一看就懂”。对于如何提高翻译水平,钱先生也认为多读多写是唯一途径,“不懂的要多查多问”。
旧雨渐去不坠用功之心
如今钱先生年事已高,已很少出门。但他对时事并不隔膜,对文化界、出版界的动态都很了解。钱先生向记者打听一些翻译同行的消息,还和我谈起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的情况,说她的作品涉及变态心理学,很不好读。这很是令人吃惊。
钱先生是寂寞的。他有一本经常摩挲手边的书――《上海作家辞典》。书是1994年出版的,十余年过去了,钱先生的许多老友相继离世,作家协会也寄来了重新修订此书的通知。书的最后一页上写满了钱先生抄录的这两年文化人士的离世信息,包括名字、去世时间和缘由等。远的如“钱钟书,1998年12月19日,北京,88岁”、“韦君宜,2002年1月26日逝于北京协和医院,84岁,脑溢血”。去年离世的有:“启功,2005年6月30日,93岁”、“梅邵武,2005年9月28日,77岁”、“巴金,2005 年10 月17 日,101 岁”等。
不过,旧雨渐去,并未让钱先生心生怨嗟之意。他仍日日用功,读书写作。目前他正在翻译德国著名诗人荷尔德林的诗歌,已进行到一百多首。钱春绮先生说:“年纪大了,但还希望多译一点。”翻译是钱先生一生的爱好,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自由撰稿人生涯的他开玩笑说自己失业三十余年,除稿费外从未有过其他收入。但他却嚼饭哺人,为国人奉献了那么多精神食粮。这是百余年前歌德、席勒、尼采诸人的幸运,也是中国几代外国文学读者的幸运。
(编辑:卢晓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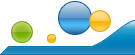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22018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2201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