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说翻译
- 剧本翻译
- 诗歌翻译
- 影视翻译
- 楹联翻译
- 广告翻译
《论语》在西方的前世今生
时间:2017/6/21 来源:翻译学研究 浏览次数:4388
中国所有的哲学家当中,在西方孔子无疑是研究得最多的一个。因为其学说已经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长达2000多年,所以想研究中国人思维方式者自然就从孔子入手了。[1]147《论语》在西方的译介、传播与研究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1]148自罗明坚(Michele Ruggleri,1543—1607)、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后,西方各界都对《论语》有着浓厚的兴趣,持续至今不衰。有关西方《论语》译介与研究的考察,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们比较感兴趣的课题,国外有谭卓恒(Cheuk-Woon Taam,1900-1956)、杜润德(Stephen W. Durrant)、郑文君(Alice W. Cheang)、史嘉柏(David Schaberg)等[1]147-165[2],而国内则有杨平、刘雪琴等[3]。
不管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大都集中论述拉丁文译本和英译本,而对其他语种的译本以及《论语》在其他国家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的关注相对较少。本文拟宏观考察《论语》在西方的前世今生,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1)考察西方《论语》译介的肇始,集中对拉丁文译本进行简要评述;(2)考察西方《论语》译介与研究的发展与成熟;(3)西方《论语》译介与研究的兴盛和拓展。后两个课题涉及到英语、法语、德语、俄语等多语种和多国家的《论语》译介与研究的情况,旨在给读者呈现《论语》在西方的全面图景。
一、西方《论语》译介的肇始
《论语》在西方的译介肇端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首先对《论语》进行翻译的是罗明坚和利玛窦。罗明坚,字复初,意大利人,明万历七年(1579)到达澳门,到过广州、肇庆等;利玛窦,号西泰,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士传教士,明万历十年(1582)来华,到过肇庆、韶州、南昌、南京等地,万历二十九年(1601)定居北京,万历三十八年病逝于北京。
1594年11月15日在给德·法比神父的信中,利玛窦提到自己所翻译的《四书》:“几年前(按为1591年)我着手迻译著名的中国《四书》为拉丁文,它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是伦理格言集,充满卓越智慧之书。”[4]143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J. Aleni)也说:“利子此时尝将中国《四书》译以西文,寄回本国,国人读而悦之,以为中邦经书能认大原不迷其主者。至今孔孟之训, 远播遐方者, 皆利子力也。”[5]204德礼贤(Pasquale d’Elia, S. J.,1890—1963)神父也提及1591年11月到1593年11月利玛窦先后将《四书》译成拉丁文。[6]253这些论述均说明,利氏曾将《四书》翻译为拉丁文。其作用便是供传教人士认识汉字,熟悉中国儒家经典,为其在中国的传教提供语言方面的准备,也从文化上对中国有所了解,更是其“适应政策”的一种体现。可惜的是,利氏所译的《四书》未刊行,并未流传下来。
而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最早《四书》拉丁文译本却是罗明坚的译本。有论者认为,罗氏与利氏大约在同时翻译《四书》,不同的是,罗氏是返回欧洲之后进行翻译,而利氏的翻译则是在中国进行的。[7]99-100张西平也指出,罗氏译《四书》时,利氏按照范礼安的要求在中国肇庆也做着同样工作。[8]107罗氏翻译的《四书》手稿现藏意大利国家图书馆,未刊行,不过其所译《大学》第一章曾于1593年刊印在罗马发行的《百科精选》(Bibliotheca Selecta qua agitur de ratione studiorum in historia, in disciplinis, in salute omnium procurand)。[9]35尽管这是《四书》在欧洲的第一次刊印,但是罗氏译文并未在欧洲产生影响,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则是,一方面传教士内部对于罗氏译文意见不一,另一方面利氏指出罗氏译文质量不高,并不可靠,因为罗氏的汉语水平一般。[10]7不过,并非所有学者均认同这种意见,例如龙伯格(Knud Lundbaek)就认为,与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2)的译文相比,罗氏的译文更为贴近朱熹的注释。[11]9-11
尽管《四书》早期译者的尝试尽管并不很成功,利氏译本佚失,而罗氏译本尽管部分得到发表,而全部得以保存意大利国家图书馆,但是这些尝试均对后来者启发很大。1624年,李玛诺神父(Manual Dias,1559—1639)确定来华传教士的四年制“课程计划”(ratio studiorum),要求传教士学习《四书》等[12]266,而郭纳爵(Inácio da Costa,1603—1666)则与其学生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6—1696)一道对利氏翻译进行完善,合作出版了《中国智慧》(Sapientia Sinica,1662)一书,内含《论语》前五章的翻译76页。[13]128
儒家学说真正在欧洲获得广泛注意得益于1687年出版由柏应理等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拉丁文译本。参与翻译和编辑的除柏应理外,尚有鲁日满(Francois de Rougemont, S.J.,1624—1676)、殷铎泽、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1624—1684)和沈福宗等,共17位传教士。该译本以张居正《四书直解》为底本,而并非根据朱熹《四书集注》,[7]102这是值得注意的。该书在欧洲影响很大,出版不久就有其他语种的转译本,如1688年即有法语转译本《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后来多次重印,1691年更有译自法语的英语转译本《孔子的道德》(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14]这些译本的刊印与发行,对于孔子及其儒家学说在欧洲的广泛传播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711年,比利时耶稣会士卫方济(Francais N·el,1651—1729)在布拉格出版《中华帝国六经》(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该书除《大学》《中庸》和《论语》外,又译出了《孟子》,所以至此西方有了《四书》的全译文;同时,该书还译有《孝经》和朱熹的《小学》①,加起来共六部,故称“中华帝国六经”。该书由普吕凯(Fran·ois-André-Adrien Pluquet,1716—1790)转译为法语,1784年以《中华帝国经典》(Les Livres classiques de l’Empire de la Chine)为书名分七卷在巴黎出版。[15]31同年,钱德明神父(Père Jean-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发表《孔子传》(La Vie de Koung tsée),该书共508页,是当时西方学者最长的一部孔子传记,杂合了《孔子家语》、《史记》、《诗经》以及其他著作中有关孔子的记述。这部著作影响巨大,后世的许多学者均征引此书。[1]148
为了更好地传教,新教传教士同样对孔子及《论语》感兴趣,也尝试翻译《论语》。《论语》首次直接从汉语翻译为英语②便是新教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所为,题目译为The Works of Confucius,包括《论语》第一至十章,译文正文共725页,包括汉语原文与译文,汉语旁边还附有英语“译音”,全书的最后一页是专有名词的拉丁文译名和英语“译音”的对照表,1809年出版于塞兰坡。[16]1828年柯大卫(David Collie)翻译的《论语》(Dialogues)在马六甲出版。[17]从体例看,马士曼的原文与译文的安排是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英译《中国经典》的先声。
二、西方《论语》译介与研究的发展与成熟
西方《论语》的译介与研究到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则进入发展与成熟期。其中的杰出代表是英国的理雅各、法国的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1835—1919)和德国的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
理雅各的《论语》翻译始于1841年,于1861年完成并出版,作为《中国经典》中的第一卷。除《论语》外,还包括《大学》《中庸》。该译本除译文外,另有一长篇绪论(Prolegomena),共136页,分六章详细阐述了各具体文本的相关情况:第一章是“中国经典综述”,包括“中国经典所涵括的书籍”和“中国经典的权威性”;第二章分析《论语》,包括“汉朝学者于《论语》的形成”、“撰写的时间、作者、计划与真实性考证”、“关于《论语》的论著”和“各类材料”;第三章分析《大学》,包括“《大学》的历史及排序上的不同”、“作者、本文与评述的区分”和“范围与价值”;第四章分析《中庸》,包括“《中庸》在《礼记》中的地位与成书时间”、“作者及其简略生平”、“完整性”和“范围与价值”;第五章论述“孔子及其直传门徒”,包括“孔子生平”、“孔子的影响与观点”和“孔子的直传门徒”;第六章则主要列出了本卷所参阅的书籍。[18] 1-136理雅各译本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汉英正文之后附以评论性注释。[19]105从下图可知,理雅各将“学而第一”翻译为“Book I. HSIO R.”,其中“第一”是翻译,而“学而”则是音译,由于那时候既没有系统的威氏拼音法(Wade-Giles System),所以他的译文中凡是音译之处,会让读者有一定困难,不过理雅各在译文前均附有拉丁文拼法与他的拼法的对照表,对读者也有一定帮助。同时,他将每一部分翻译成“Chapter”,即章,如Chapter I、Chapter II等,而每一节则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比如下图中的1、2、3等。汉英正文之后便是详尽的评论性注释,这样做当然显得繁琐,但是对于外国读者而言,无疑是非常有帮助的。费乐仁认为,翻译作品如果用这种方式呈现,也就是将汉语原文、译文与评论性注释进行理雅各这样的三栏处理,就会形成写作学(grammatology)上一种特殊的动态,读者可以因此自行判断翻译是否得当,是否可更雅致,论证是否恰切。[19]105此前的翻译最多征引两种注疏:一是朱熹的注疏,在中国学术界影响非常巨大;二是张居正的注疏,因为张居正是写给十岁的少年万历皇帝阅读的,所以相对简易。而理雅各则征引了300多种重要儒家注疏,融入了古往今来的儒家学术传统,水平非常高。[19]105对于外国读者而言,这种方式无疑是一种非常便捷而又可以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和典籍的方式,对于今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实践无疑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理雅各《论语》等译本的优势当然不仅限于此,费乐仁列出了十五种之多[19]102-111,其余的不在本文探讨范畴内,故在此不赘。理雅各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国经典》的翻译直接启示了后来者,例如法国的顾赛芬、英国的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德国的卫礼贤和中国的辜鸿铭等等。
顾赛芬翻译的中国典籍沿袭了理雅各的很多做法,例如汉语语段置于页面上端,而其后则紧接着用法语的读音来为汉字注音,在其后才是法语和拉丁语并列的译文,同样用数字为篇、章编号,而明显减少的是大段大段的注解。费乐仁指出,顾赛芬的翻译大体上继承了理雅各的翻译制例,为古籍中的每一个汉字都注出了法语读音,而且提供了法语与拉丁文并列的译文范本,使其成为了法语、拉丁语读者捧读的“经典翻译”。[20]111-113
辜鸿铭在其“英译《论语》序”中提到,他之所以要翻译《论语》,是因为他对理雅各的译文非常不满意,认为他的译文不达意。在翻译《论语》时,辜鸿铭为了使他所诠释的儒家观点能影响处于另一种意识形态环境下的西方读者,他在表达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时,尽量保持西化的语言特色,消除西方读者的陌生感,从而希望勾起西方读者的阅读欲望。辜鸿铭在翻译时,除语言的西化外,还夹注一段西方哲人的话,以便读者对照理解。[21]345-347
苏慧廉在其序言中,直接提到理雅各英译本、辜鸿铭英译本、晁德笠(Angelo Zottoli,1826—1902)法译本和顾赛芬法译本,尤其是理雅各英译本对其译作的贡献。[22]II-III苏慧廉是逐字逐句对《论语》进行英译的,并附上了详尽的注释(如图2所示)。
卫礼贤翻译的《论语》曾有三个版本,卫氏《论语》德译本的第一稿于1904年发表在《东方世界》(Die Welt des Ostens)的续篇上,这是青岛出版的报纸《德国—亚洲瞭望》(Deutsch-Asiatische Warte)的副刊[23]467;而第三稿则于1910年在耶拿出版社出版。[24]德国对于孔子及其《论语》的研究最远可以追溯到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及其弟子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等。莱布尼兹景仰中国的精神文明,赞叹孔子思想的伟大与高洁,认为东方秩序良好的国家可作为充满怨恨和仇恶心理的西方国家的模范。[25]49戴维斯(Walter W. Davis)则认为孔子思想的引入使莱布尼兹看到了在世界宗教中发现共同真理的可能,这些真理将使全世界的人民连为一体,而且其观点影响了同时代的其他思想精英,尤其是其弟子、哲学家沃尔夫。[26]535-36而第一部《论语》德译本则出自朔特(Wilhelm Schott,1802—1889)[27]164
莱布尼兹也好,朔特也罢,他们对于孔子及其《论语》的诠释和认识,由于时代和自身的局限性,他们并未能到中国来亲炙中国文化,所以其言论和译作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成为沉积,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卫礼贤的《论语》德译本则与此不同,它直到21世纪依旧是德语世界的标准之作。对于理雅各的翻译方法与原则,卫礼贤既有继承又有超越,[19]115-116这可能是其译作生命力旺盛的部分原因。
孔子及其《论语》中揭示的理性与人性因子,同样是启蒙知识分子的追求目标。张涛指出,在启蒙时代的欧洲,孔子宣扬的人本主义和开明政治掀起了一股热潮,成为欧洲思想界竞相学习、研读的范本。[28]23其中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尤其引人瞩目,其“慕华”(sinophile)情结终生不渝,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厚爱慕贯穿他所有作品,即便是中国热在法国已经露出衰落的迹象,他始终信赖孔子的理想观念。[29]1050罗柏森(Arnold H. Rowbotham)指出,孔子学说从三个重要方面影响了17、18世纪的欧洲思想:1)助长了针对基督教基本原则的批判精神、2)唤醒了人们对个人与国家间关系问题的兴趣、3)确立了学者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30]238
孔子学说在欧洲不只是收到热情欢迎与推崇,也有反对和质疑之声不时发出,基督教内部更是如此。属于天主教的耶稣会士对孔子及其学说颂扬有加,而该教的其他分支为了抢夺教会主导权却贬低耶稣会报告的可信度。[28]26孔诰烽(Ho-Fung Hung)指出,耶稣会的中国和孔子观因为教会内部的斗争而在其中一蹶不振,却由于深得欧洲启蒙思想家的青睐而在世俗社会影响深远;欧洲人质疑和反对孔子学说分三个阶段:1)耶稣会与方济各各会等其他分支的矛盾为第一阶段;2)18世纪后半叶的法国百科全书派思想家发起了第二轮大抨击,如康德称中国人头脑中从无美德与道德观念,而黑格尔认为孔子思想是极为乏味的迷信和行为规范;3)19世纪,因东西方政治格局的变化、欧洲民族主义的兴盛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兴起,孔子学说乃至中国的整个思想制度都被视为欧洲的对立面,而成为低劣文化的代表,这是第三阶段。[31]257-60, 261-62, 268-74
这时期还有其他一些《论语》英译本③,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林语堂和韦利(Arthur Waley,1888—1966)翻译的《论语》。西方学者认为,韦氏的《论语》英译本可能是西方最具才学的(the most briliant)的译本,不管其译文的对错与否,均有意义,其长篇导论和译文中的注释也引人入胜,原因是他征引了许多中国学者关于《论语》的最好注疏。可惜的是,他很少列出引文的出处。[32]62林氏对孔子及其《论语》的思考集体在他的著作《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中,这是林氏系统向西方介绍孔子思想的著作,除“序言”外,均是林氏从各种典籍中选辑出来的,是孔子“述而不作”的完美体现。[33]1-2 这一选编本对于西方读者全面认识孔子及其《论语》有着极为积极的意义。谭卓恒指出,林氏的方法是很新的,其翻译也是准确、流畅而鲜活的,与过去将孔子刻画为保守、严厉而不苟言笑之人相比,林氏将孔子描画为富含人性、睿智而幽默的君子,有着自己明确的喜好;当然,林氏这样处理的不足之处在于,孔子显得比他本人更古怪。[1]154
17世纪初欧洲人在北美大陆开辟殖民地,孔子及其学说也随之传播至北美。爱默生(Ralph W. Emerson,1803—1882)盛赞孔子是“世界的荣耀”和“哲学中的华盛顿”,并认为孔子可与耶稣、苏格拉底媲美。[34] 205-06梭罗(Henry D. Thoreau,1817—1862)同样非常推崇孔子,他将孔子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与现实经历的精炼总结(pithy crystallization)相提并论。[35]203中外学者均发现,梭罗名著《瓦尔登湖》中多处征引包括《论语》在内的儒家典籍。[36]20-24
三、西方《论语》译介与研究的兴盛与拓展
20世纪后半叶无疑迎来了西方《论语》译介与研究的兴盛与拓展期,主要表现在《论语》译本越来越来,与孔子和《论语》相关的专著也层出不群,并且这种趋势不仅限于英语国家,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如此。
第一位需要注意的是庞德(Ezra Pound,1885—1972),他于1951年翻译出版了《孔子:大学、中庸和论语》(Confucius: the Great digest, the Unwobbling pivot, the Analects)。[37]庞德对于中国文字和中国典籍的解读以及他的创作和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中外均有很多深入的研究。相比以前的翻译,从标题上看庞德的不同是他将《大学》和《中庸》分别译为了“the Great Digest”和“the Unwobbling Pivot”。李欧梵曾提到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1916—1999)从严复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群学肄言》(Study of Sociology,目前通译《社会学研究》)的理解入手,将这本书与中国儒家经典的《四书》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以此讨论斯宾塞的“科学”概念与严复思想中儒家遗产之间的某种亲缘关系,例如It was precisely cultivation of the sciences which led to that purgation of all the beclouding by the passions dreamed of by the ancient sages, or, alternatively, it was precisely Western science which presupposed the moral qualities, the adherence to the “mean” (Ezra Pound’s “Unwobbling Pivot”) described i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38]22④ 李欧梵坦诚,对于这段话他有很多疑虑,例如斯宾塞的“社会学”如何和 中国的道德价值或《中庸》中所预设和阐述的德行联系起来,不知道庞德是谁,对英文单词“Unwobbling Pivot”的意思也一窍不通,而几十年后史华慈对于庞德术语的参考依然让他好奇;通过一遍遍的阅读,他发现这段话里,史华慈事实上为严复接受是不是得科学思想提出了两种解释并将其构成一种双层论据:(1)作为西方思想家的斯宾塞重新认可了严复所认同的那些业已被视作有些保守和传统的中国先哲的道德洞见;(2)斯宾塞“科学”方法中的“诚意”内涵又向严复证明了即使西方真正的科学知识也都建立在某些道德原则上,可以延伸出某种中西共享的道德资源。因此,严复的理由通过史华慈的话语表达出来后,典雅的中国词汇(诚意)就使史华慈式的精心遣词造句显得更为深邃、复杂。[38]22-24
此后,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多的读者和学者注意到中国,也更为关心中国文化,因此英美国家以及全球范围内都有一股认识、深入解读代表中国文化精髓的中国典籍的热潮,孔子的《论语》更是不断被翻译出来,如魏鲁男(James R. Ware)、陈荣捷、傅罗仁(Lawrence Faucett)、刘殿爵(D. C. Lau)、华霭仁(Irene Bloom)、柯汤姆(Thomas Cleary)、窦雷蒙(Raymond Dawson)、黄继忠(Chichung Huang)、李克曼(Pierre Ryckmans,笔名Simon Leys)、安乐哲(Roger T. Ames)和罗思文(Henry Rosemont, Jr.)、白牧之(E. Bruce Brooks)和白妙子(A. Taeko Brooks)夫妇、亨大卫(David Hinton)、李祥甫(David H. Li)、森舸澜(Edward G. Slingerland)和华兹生(Burton Watson)等。⑤其中影响更大的则分别是刘殿爵、柯汤姆、李克曼、安乐哲和罗思文、白牧之和白妙子夫妇以及森舸澜的译本,中外学者均有较为深入的讨论与研究。
斯洛伐克汉学家高利克((Marián Gálik,1933—)曾撰文详细介绍孔子和儒学在波西米亚和斯洛伐克的接受,指出孔子和儒学在斯洛伐克的接受已有280年历史,出现了卫方济和普实克(Jaroslav Prü·ek,1906—1980)等著名中国文化传播者。[39]180-190《论语》在俄罗斯的翻译始于1729年,至今已有285年历史,不计研究儒学的专著或论文中所出现的部分《论语》译文,其译本至少有17个。[40]96-102李明滨指出,贝列罗莫夫(Переломов,俄籍华裔,汉语姓名稽辽拉)1993年出版的专著《孔子·生平、学说、命运》,对孔子及其儒学进行了全面、系统而深入的讨论,是俄国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部孔子研究的专著。[41]55-56稽辽拉的《论语》翻译颇有特色,遇到疑难之处,他将各种语种(包括英语、德语、日语、韩语、汉语和俄语)的译例举出来以方便读者进行比较。[42]356-360托尔斯泰对孔子的崇敬之情更是学者们热衷讨论的话题,如米勒(Rene Fueloep-Miller)称孔子为托翁的“开明导师之一”[43]113-14。芬兰对于孔子及其学说也有很浓厚的兴趣,第一本中国儒家文化典籍的翻译和介绍就是柯和宁(Kalle Korhonen)翻译的《大学:儒家世界观导读》(Suuri Oppi: Johdatus Kunfutselaiseen el·m·nkatsomukseen),1921出版。其中《大学》的翻译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内容,更多篇幅是介绍孔子的生平以及孔子的思想。[44]32 王为义(Toivo Koskikallio)的译本《孔子:论语》1958年出版,其后多次再版,其翻译根据传统分篇章目的方法,标注了篇目名称,概括该章主题如“关于学习”(Opiskelusta,学而),“关于管理”(Hallitustoimista,为政),“关于节礼”(Juhalamenoista,八侑),“邻里之爱”(Naapmirakkaus,里仁)。[44]55-56
孔子及其学说在西方的兴盛和拓展还表现在很多华裔学者的加入以及研究主题的拓展方面。金安平的《孔子:喧嚣时代的孤独哲人》(The Authentic Confucius)完成于2007年,其最主要的史料来源是《论语》与《左传》,原因是《论语》是与孔子最密切相关的作品,而《左传》也说明孔子的渊源。[45]13-15在此还得提到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因为司马迁是最善于以想象力重构过去的史学家,在追寻历史与历史人物的过程中,他不会让历史记录成为负担,也不会为编年史的阙漏所困扰,而金安平写的孔子生平,主要在于回应司马迁,所以她未采取司马迁连续叙事的笔法,而是在叙事中留下空白,以此来反映史料的阙如。[46]15-16从某种意义上说,金安平对于司马迁的叙述是表示怀疑的。她指出,司马迁是第一位试图将孔子周游列国的零散故事组织成连贯叙事的史学家,其做法是借由添加敏锐的眼光与戏剧性的事件来增益故事,为了使故事完整,他不惜安排各种情节转折以填补漏洞,因此司马迁的叙述既过分改写了孔子的事迹,又过度弥补了污损孔子名声所带来的问题,更是存在着逻辑问题。[45]107-108作为国际著名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妻子,金安平无疑在历史写作上受到史景迁的影响,正是这一因素使得她的著作有着与史景迁史学著作般的高度可读性。[46]
另一部值得一提的著作是孟久丽(Julia K. Murray)的《道德镜鉴:中国叙述性图画与儒家意识形态》[47],她将孔子及其《论语》的研究在国外拓展到了完全不为人注意的方面,即叙述性图画与儒家意识形态(学说),其主旨即探讨图像在典籍流传中的功能,在书写中国叙述性图画史之时,分析社会精英阶层如何运用图像宣扬和维护儒家价值观。[48]126孟久丽通过考察《孔子圣迹图》的渊源和流传,从而揭示出了孔子及其学说是如何深入中国人的心理和深层结构的。[49]269-300
四、余论
《论语》在西方的译介、传播、接受与研究的过程,是中国文化在西方译介、传播与接受的一个缩影。从16 世纪至今,《论语》在西方已经传播了400 多年,这期间有很多方面还未有人予以关注,本文只是尝试初略梳理其传播简史,除关注传播较为普及和充分的几个国家如美国、英国之外,也将眼光拓展到《论语》在法国、德国、俄国,甚至斯洛伐克、芬兰等国家的译介、流传与研究上。
后续的研究除了宏观方面,更应该关注微观方面:如(1)《论语》书籍是如何传入西方的,其版本如何,其中哪些人起到了关键作用;(2)各种译本依据的是哪种注疏(释),译者为什么选择了这种(些)注疏,而不是另外的注疏;(3)译本的完成是否得到了中国学者的帮助,其依赖性有多大;(4)传播中哪些因素更重要,其原因是什么等等。
尤为重要的是,以往译本所参考的《论语》文本并非均为权威注疏,而且当代的优秀研究成果并未得到及时的利用。中国学者对国内状况更为熟悉,不管是对古代还是现当代的注疏和研究成果,都容易获取和掌握。因此,中国学者可以与外国学者(包括华裔学者)合作,将《论语》及其最新研究成果推介到海外,并利用更为精当而权威的传统和现代注疏对《论语》重新进行英译,从而推出更为可读而经典的新译作。
不管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大都集中论述拉丁文译本和英译本,而对其他语种的译本以及《论语》在其他国家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的关注相对较少。本文拟宏观考察《论语》在西方的前世今生,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1)考察西方《论语》译介的肇始,集中对拉丁文译本进行简要评述;(2)考察西方《论语》译介与研究的发展与成熟;(3)西方《论语》译介与研究的兴盛和拓展。后两个课题涉及到英语、法语、德语、俄语等多语种和多国家的《论语》译介与研究的情况,旨在给读者呈现《论语》在西方的全面图景。
一、西方《论语》译介的肇始
《论语》在西方的译介肇端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首先对《论语》进行翻译的是罗明坚和利玛窦。罗明坚,字复初,意大利人,明万历七年(1579)到达澳门,到过广州、肇庆等;利玛窦,号西泰,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士传教士,明万历十年(1582)来华,到过肇庆、韶州、南昌、南京等地,万历二十九年(1601)定居北京,万历三十八年病逝于北京。
1594年11月15日在给德·法比神父的信中,利玛窦提到自己所翻译的《四书》:“几年前(按为1591年)我着手迻译著名的中国《四书》为拉丁文,它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是伦理格言集,充满卓越智慧之书。”[4]143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J. Aleni)也说:“利子此时尝将中国《四书》译以西文,寄回本国,国人读而悦之,以为中邦经书能认大原不迷其主者。至今孔孟之训, 远播遐方者, 皆利子力也。”[5]204德礼贤(Pasquale d’Elia, S. J.,1890—1963)神父也提及1591年11月到1593年11月利玛窦先后将《四书》译成拉丁文。[6]253这些论述均说明,利氏曾将《四书》翻译为拉丁文。其作用便是供传教人士认识汉字,熟悉中国儒家经典,为其在中国的传教提供语言方面的准备,也从文化上对中国有所了解,更是其“适应政策”的一种体现。可惜的是,利氏所译的《四书》未刊行,并未流传下来。
而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最早《四书》拉丁文译本却是罗明坚的译本。有论者认为,罗氏与利氏大约在同时翻译《四书》,不同的是,罗氏是返回欧洲之后进行翻译,而利氏的翻译则是在中国进行的。[7]99-100张西平也指出,罗氏译《四书》时,利氏按照范礼安的要求在中国肇庆也做着同样工作。[8]107罗氏翻译的《四书》手稿现藏意大利国家图书馆,未刊行,不过其所译《大学》第一章曾于1593年刊印在罗马发行的《百科精选》(Bibliotheca Selecta qua agitur de ratione studiorum in historia, in disciplinis, in salute omnium procurand)。[9]35尽管这是《四书》在欧洲的第一次刊印,但是罗氏译文并未在欧洲产生影响,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则是,一方面传教士内部对于罗氏译文意见不一,另一方面利氏指出罗氏译文质量不高,并不可靠,因为罗氏的汉语水平一般。[10]7不过,并非所有学者均认同这种意见,例如龙伯格(Knud Lundbaek)就认为,与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2)的译文相比,罗氏的译文更为贴近朱熹的注释。[11]9-11
尽管《四书》早期译者的尝试尽管并不很成功,利氏译本佚失,而罗氏译本尽管部分得到发表,而全部得以保存意大利国家图书馆,但是这些尝试均对后来者启发很大。1624年,李玛诺神父(Manual Dias,1559—1639)确定来华传教士的四年制“课程计划”(ratio studiorum),要求传教士学习《四书》等[12]266,而郭纳爵(Inácio da Costa,1603—1666)则与其学生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6—1696)一道对利氏翻译进行完善,合作出版了《中国智慧》(Sapientia Sinica,1662)一书,内含《论语》前五章的翻译76页。[13]128
儒家学说真正在欧洲获得广泛注意得益于1687年出版由柏应理等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拉丁文译本。参与翻译和编辑的除柏应理外,尚有鲁日满(Francois de Rougemont, S.J.,1624—1676)、殷铎泽、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1624—1684)和沈福宗等,共17位传教士。该译本以张居正《四书直解》为底本,而并非根据朱熹《四书集注》,[7]102这是值得注意的。该书在欧洲影响很大,出版不久就有其他语种的转译本,如1688年即有法语转译本《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后来多次重印,1691年更有译自法语的英语转译本《孔子的道德》(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14]这些译本的刊印与发行,对于孔子及其儒家学说在欧洲的广泛传播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711年,比利时耶稣会士卫方济(Francais N·el,1651—1729)在布拉格出版《中华帝国六经》(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该书除《大学》《中庸》和《论语》外,又译出了《孟子》,所以至此西方有了《四书》的全译文;同时,该书还译有《孝经》和朱熹的《小学》①,加起来共六部,故称“中华帝国六经”。该书由普吕凯(Fran·ois-André-Adrien Pluquet,1716—1790)转译为法语,1784年以《中华帝国经典》(Les Livres classiques de l’Empire de la Chine)为书名分七卷在巴黎出版。[15]31同年,钱德明神父(Père Jean-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发表《孔子传》(La Vie de Koung tsée),该书共508页,是当时西方学者最长的一部孔子传记,杂合了《孔子家语》、《史记》、《诗经》以及其他著作中有关孔子的记述。这部著作影响巨大,后世的许多学者均征引此书。[1]148
为了更好地传教,新教传教士同样对孔子及《论语》感兴趣,也尝试翻译《论语》。《论语》首次直接从汉语翻译为英语②便是新教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所为,题目译为The Works of Confucius,包括《论语》第一至十章,译文正文共725页,包括汉语原文与译文,汉语旁边还附有英语“译音”,全书的最后一页是专有名词的拉丁文译名和英语“译音”的对照表,1809年出版于塞兰坡。[16]1828年柯大卫(David Collie)翻译的《论语》(Dialogues)在马六甲出版。[17]从体例看,马士曼的原文与译文的安排是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英译《中国经典》的先声。
二、西方《论语》译介与研究的发展与成熟
西方《论语》的译介与研究到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则进入发展与成熟期。其中的杰出代表是英国的理雅各、法国的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1835—1919)和德国的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
理雅各的《论语》翻译始于1841年,于1861年完成并出版,作为《中国经典》中的第一卷。除《论语》外,还包括《大学》《中庸》。该译本除译文外,另有一长篇绪论(Prolegomena),共136页,分六章详细阐述了各具体文本的相关情况:第一章是“中国经典综述”,包括“中国经典所涵括的书籍”和“中国经典的权威性”;第二章分析《论语》,包括“汉朝学者于《论语》的形成”、“撰写的时间、作者、计划与真实性考证”、“关于《论语》的论著”和“各类材料”;第三章分析《大学》,包括“《大学》的历史及排序上的不同”、“作者、本文与评述的区分”和“范围与价值”;第四章分析《中庸》,包括“《中庸》在《礼记》中的地位与成书时间”、“作者及其简略生平”、“完整性”和“范围与价值”;第五章论述“孔子及其直传门徒”,包括“孔子生平”、“孔子的影响与观点”和“孔子的直传门徒”;第六章则主要列出了本卷所参阅的书籍。[18] 1-136理雅各译本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汉英正文之后附以评论性注释。[19]105从下图可知,理雅各将“学而第一”翻译为“Book I. HSIO R.”,其中“第一”是翻译,而“学而”则是音译,由于那时候既没有系统的威氏拼音法(Wade-Giles System),所以他的译文中凡是音译之处,会让读者有一定困难,不过理雅各在译文前均附有拉丁文拼法与他的拼法的对照表,对读者也有一定帮助。同时,他将每一部分翻译成“Chapter”,即章,如Chapter I、Chapter II等,而每一节则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比如下图中的1、2、3等。汉英正文之后便是详尽的评论性注释,这样做当然显得繁琐,但是对于外国读者而言,无疑是非常有帮助的。费乐仁认为,翻译作品如果用这种方式呈现,也就是将汉语原文、译文与评论性注释进行理雅各这样的三栏处理,就会形成写作学(grammatology)上一种特殊的动态,读者可以因此自行判断翻译是否得当,是否可更雅致,论证是否恰切。[19]105此前的翻译最多征引两种注疏:一是朱熹的注疏,在中国学术界影响非常巨大;二是张居正的注疏,因为张居正是写给十岁的少年万历皇帝阅读的,所以相对简易。而理雅各则征引了300多种重要儒家注疏,融入了古往今来的儒家学术传统,水平非常高。[19]105对于外国读者而言,这种方式无疑是一种非常便捷而又可以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和典籍的方式,对于今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实践无疑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理雅各《论语》等译本的优势当然不仅限于此,费乐仁列出了十五种之多[19]102-111,其余的不在本文探讨范畴内,故在此不赘。理雅各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国经典》的翻译直接启示了后来者,例如法国的顾赛芬、英国的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德国的卫礼贤和中国的辜鸿铭等等。
顾赛芬翻译的中国典籍沿袭了理雅各的很多做法,例如汉语语段置于页面上端,而其后则紧接着用法语的读音来为汉字注音,在其后才是法语和拉丁语并列的译文,同样用数字为篇、章编号,而明显减少的是大段大段的注解。费乐仁指出,顾赛芬的翻译大体上继承了理雅各的翻译制例,为古籍中的每一个汉字都注出了法语读音,而且提供了法语与拉丁文并列的译文范本,使其成为了法语、拉丁语读者捧读的“经典翻译”。[20]111-113
辜鸿铭在其“英译《论语》序”中提到,他之所以要翻译《论语》,是因为他对理雅各的译文非常不满意,认为他的译文不达意。在翻译《论语》时,辜鸿铭为了使他所诠释的儒家观点能影响处于另一种意识形态环境下的西方读者,他在表达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时,尽量保持西化的语言特色,消除西方读者的陌生感,从而希望勾起西方读者的阅读欲望。辜鸿铭在翻译时,除语言的西化外,还夹注一段西方哲人的话,以便读者对照理解。[21]345-347
苏慧廉在其序言中,直接提到理雅各英译本、辜鸿铭英译本、晁德笠(Angelo Zottoli,1826—1902)法译本和顾赛芬法译本,尤其是理雅各英译本对其译作的贡献。[22]II-III苏慧廉是逐字逐句对《论语》进行英译的,并附上了详尽的注释(如图2所示)。
卫礼贤翻译的《论语》曾有三个版本,卫氏《论语》德译本的第一稿于1904年发表在《东方世界》(Die Welt des Ostens)的续篇上,这是青岛出版的报纸《德国—亚洲瞭望》(Deutsch-Asiatische Warte)的副刊[23]467;而第三稿则于1910年在耶拿出版社出版。[24]德国对于孔子及其《论语》的研究最远可以追溯到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及其弟子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等。莱布尼兹景仰中国的精神文明,赞叹孔子思想的伟大与高洁,认为东方秩序良好的国家可作为充满怨恨和仇恶心理的西方国家的模范。[25]49戴维斯(Walter W. Davis)则认为孔子思想的引入使莱布尼兹看到了在世界宗教中发现共同真理的可能,这些真理将使全世界的人民连为一体,而且其观点影响了同时代的其他思想精英,尤其是其弟子、哲学家沃尔夫。[26]535-36而第一部《论语》德译本则出自朔特(Wilhelm Schott,1802—1889)[27]164
莱布尼兹也好,朔特也罢,他们对于孔子及其《论语》的诠释和认识,由于时代和自身的局限性,他们并未能到中国来亲炙中国文化,所以其言论和译作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成为沉积,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卫礼贤的《论语》德译本则与此不同,它直到21世纪依旧是德语世界的标准之作。对于理雅各的翻译方法与原则,卫礼贤既有继承又有超越,[19]115-116这可能是其译作生命力旺盛的部分原因。
孔子及其《论语》中揭示的理性与人性因子,同样是启蒙知识分子的追求目标。张涛指出,在启蒙时代的欧洲,孔子宣扬的人本主义和开明政治掀起了一股热潮,成为欧洲思想界竞相学习、研读的范本。[28]23其中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尤其引人瞩目,其“慕华”(sinophile)情结终生不渝,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厚爱慕贯穿他所有作品,即便是中国热在法国已经露出衰落的迹象,他始终信赖孔子的理想观念。[29]1050罗柏森(Arnold H. Rowbotham)指出,孔子学说从三个重要方面影响了17、18世纪的欧洲思想:1)助长了针对基督教基本原则的批判精神、2)唤醒了人们对个人与国家间关系问题的兴趣、3)确立了学者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30]238
孔子学说在欧洲不只是收到热情欢迎与推崇,也有反对和质疑之声不时发出,基督教内部更是如此。属于天主教的耶稣会士对孔子及其学说颂扬有加,而该教的其他分支为了抢夺教会主导权却贬低耶稣会报告的可信度。[28]26孔诰烽(Ho-Fung Hung)指出,耶稣会的中国和孔子观因为教会内部的斗争而在其中一蹶不振,却由于深得欧洲启蒙思想家的青睐而在世俗社会影响深远;欧洲人质疑和反对孔子学说分三个阶段:1)耶稣会与方济各各会等其他分支的矛盾为第一阶段;2)18世纪后半叶的法国百科全书派思想家发起了第二轮大抨击,如康德称中国人头脑中从无美德与道德观念,而黑格尔认为孔子思想是极为乏味的迷信和行为规范;3)19世纪,因东西方政治格局的变化、欧洲民族主义的兴盛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兴起,孔子学说乃至中国的整个思想制度都被视为欧洲的对立面,而成为低劣文化的代表,这是第三阶段。[31]257-60, 261-62, 268-74
这时期还有其他一些《论语》英译本③,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林语堂和韦利(Arthur Waley,1888—1966)翻译的《论语》。西方学者认为,韦氏的《论语》英译本可能是西方最具才学的(the most briliant)的译本,不管其译文的对错与否,均有意义,其长篇导论和译文中的注释也引人入胜,原因是他征引了许多中国学者关于《论语》的最好注疏。可惜的是,他很少列出引文的出处。[32]62林氏对孔子及其《论语》的思考集体在他的著作《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中,这是林氏系统向西方介绍孔子思想的著作,除“序言”外,均是林氏从各种典籍中选辑出来的,是孔子“述而不作”的完美体现。[33]1-2 这一选编本对于西方读者全面认识孔子及其《论语》有着极为积极的意义。谭卓恒指出,林氏的方法是很新的,其翻译也是准确、流畅而鲜活的,与过去将孔子刻画为保守、严厉而不苟言笑之人相比,林氏将孔子描画为富含人性、睿智而幽默的君子,有着自己明确的喜好;当然,林氏这样处理的不足之处在于,孔子显得比他本人更古怪。[1]154
17世纪初欧洲人在北美大陆开辟殖民地,孔子及其学说也随之传播至北美。爱默生(Ralph W. Emerson,1803—1882)盛赞孔子是“世界的荣耀”和“哲学中的华盛顿”,并认为孔子可与耶稣、苏格拉底媲美。[34] 205-06梭罗(Henry D. Thoreau,1817—1862)同样非常推崇孔子,他将孔子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与现实经历的精炼总结(pithy crystallization)相提并论。[35]203中外学者均发现,梭罗名著《瓦尔登湖》中多处征引包括《论语》在内的儒家典籍。[36]20-24
三、西方《论语》译介与研究的兴盛与拓展
20世纪后半叶无疑迎来了西方《论语》译介与研究的兴盛与拓展期,主要表现在《论语》译本越来越来,与孔子和《论语》相关的专著也层出不群,并且这种趋势不仅限于英语国家,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如此。
第一位需要注意的是庞德(Ezra Pound,1885—1972),他于1951年翻译出版了《孔子:大学、中庸和论语》(Confucius: the Great digest, the Unwobbling pivot, the Analects)。[37]庞德对于中国文字和中国典籍的解读以及他的创作和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中外均有很多深入的研究。相比以前的翻译,从标题上看庞德的不同是他将《大学》和《中庸》分别译为了“the Great Digest”和“the Unwobbling Pivot”。李欧梵曾提到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1916—1999)从严复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群学肄言》(Study of Sociology,目前通译《社会学研究》)的理解入手,将这本书与中国儒家经典的《四书》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以此讨论斯宾塞的“科学”概念与严复思想中儒家遗产之间的某种亲缘关系,例如It was precisely cultivation of the sciences which led to that purgation of all the beclouding by the passions dreamed of by the ancient sages, or, alternatively, it was precisely Western science which presupposed the moral qualities, the adherence to the “mean” (Ezra Pound’s “Unwobbling Pivot”) described i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38]22④ 李欧梵坦诚,对于这段话他有很多疑虑,例如斯宾塞的“社会学”如何和 中国的道德价值或《中庸》中所预设和阐述的德行联系起来,不知道庞德是谁,对英文单词“Unwobbling Pivot”的意思也一窍不通,而几十年后史华慈对于庞德术语的参考依然让他好奇;通过一遍遍的阅读,他发现这段话里,史华慈事实上为严复接受是不是得科学思想提出了两种解释并将其构成一种双层论据:(1)作为西方思想家的斯宾塞重新认可了严复所认同的那些业已被视作有些保守和传统的中国先哲的道德洞见;(2)斯宾塞“科学”方法中的“诚意”内涵又向严复证明了即使西方真正的科学知识也都建立在某些道德原则上,可以延伸出某种中西共享的道德资源。因此,严复的理由通过史华慈的话语表达出来后,典雅的中国词汇(诚意)就使史华慈式的精心遣词造句显得更为深邃、复杂。[38]22-24
此后,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多的读者和学者注意到中国,也更为关心中国文化,因此英美国家以及全球范围内都有一股认识、深入解读代表中国文化精髓的中国典籍的热潮,孔子的《论语》更是不断被翻译出来,如魏鲁男(James R. Ware)、陈荣捷、傅罗仁(Lawrence Faucett)、刘殿爵(D. C. Lau)、华霭仁(Irene Bloom)、柯汤姆(Thomas Cleary)、窦雷蒙(Raymond Dawson)、黄继忠(Chichung Huang)、李克曼(Pierre Ryckmans,笔名Simon Leys)、安乐哲(Roger T. Ames)和罗思文(Henry Rosemont, Jr.)、白牧之(E. Bruce Brooks)和白妙子(A. Taeko Brooks)夫妇、亨大卫(David Hinton)、李祥甫(David H. Li)、森舸澜(Edward G. Slingerland)和华兹生(Burton Watson)等。⑤其中影响更大的则分别是刘殿爵、柯汤姆、李克曼、安乐哲和罗思文、白牧之和白妙子夫妇以及森舸澜的译本,中外学者均有较为深入的讨论与研究。
斯洛伐克汉学家高利克((Marián Gálik,1933—)曾撰文详细介绍孔子和儒学在波西米亚和斯洛伐克的接受,指出孔子和儒学在斯洛伐克的接受已有280年历史,出现了卫方济和普实克(Jaroslav Prü·ek,1906—1980)等著名中国文化传播者。[39]180-190《论语》在俄罗斯的翻译始于1729年,至今已有285年历史,不计研究儒学的专著或论文中所出现的部分《论语》译文,其译本至少有17个。[40]96-102李明滨指出,贝列罗莫夫(Переломов,俄籍华裔,汉语姓名稽辽拉)1993年出版的专著《孔子·生平、学说、命运》,对孔子及其儒学进行了全面、系统而深入的讨论,是俄国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部孔子研究的专著。[41]55-56稽辽拉的《论语》翻译颇有特色,遇到疑难之处,他将各种语种(包括英语、德语、日语、韩语、汉语和俄语)的译例举出来以方便读者进行比较。[42]356-360托尔斯泰对孔子的崇敬之情更是学者们热衷讨论的话题,如米勒(Rene Fueloep-Miller)称孔子为托翁的“开明导师之一”[43]113-14。芬兰对于孔子及其学说也有很浓厚的兴趣,第一本中国儒家文化典籍的翻译和介绍就是柯和宁(Kalle Korhonen)翻译的《大学:儒家世界观导读》(Suuri Oppi: Johdatus Kunfutselaiseen el·m·nkatsomukseen),1921出版。其中《大学》的翻译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内容,更多篇幅是介绍孔子的生平以及孔子的思想。[44]32 王为义(Toivo Koskikallio)的译本《孔子:论语》1958年出版,其后多次再版,其翻译根据传统分篇章目的方法,标注了篇目名称,概括该章主题如“关于学习”(Opiskelusta,学而),“关于管理”(Hallitustoimista,为政),“关于节礼”(Juhalamenoista,八侑),“邻里之爱”(Naapmirakkaus,里仁)。[44]55-56
孔子及其学说在西方的兴盛和拓展还表现在很多华裔学者的加入以及研究主题的拓展方面。金安平的《孔子:喧嚣时代的孤独哲人》(The Authentic Confucius)完成于2007年,其最主要的史料来源是《论语》与《左传》,原因是《论语》是与孔子最密切相关的作品,而《左传》也说明孔子的渊源。[45]13-15在此还得提到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因为司马迁是最善于以想象力重构过去的史学家,在追寻历史与历史人物的过程中,他不会让历史记录成为负担,也不会为编年史的阙漏所困扰,而金安平写的孔子生平,主要在于回应司马迁,所以她未采取司马迁连续叙事的笔法,而是在叙事中留下空白,以此来反映史料的阙如。[46]15-16从某种意义上说,金安平对于司马迁的叙述是表示怀疑的。她指出,司马迁是第一位试图将孔子周游列国的零散故事组织成连贯叙事的史学家,其做法是借由添加敏锐的眼光与戏剧性的事件来增益故事,为了使故事完整,他不惜安排各种情节转折以填补漏洞,因此司马迁的叙述既过分改写了孔子的事迹,又过度弥补了污损孔子名声所带来的问题,更是存在着逻辑问题。[45]107-108作为国际著名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妻子,金安平无疑在历史写作上受到史景迁的影响,正是这一因素使得她的著作有着与史景迁史学著作般的高度可读性。[46]
另一部值得一提的著作是孟久丽(Julia K. Murray)的《道德镜鉴:中国叙述性图画与儒家意识形态》[47],她将孔子及其《论语》的研究在国外拓展到了完全不为人注意的方面,即叙述性图画与儒家意识形态(学说),其主旨即探讨图像在典籍流传中的功能,在书写中国叙述性图画史之时,分析社会精英阶层如何运用图像宣扬和维护儒家价值观。[48]126孟久丽通过考察《孔子圣迹图》的渊源和流传,从而揭示出了孔子及其学说是如何深入中国人的心理和深层结构的。[49]269-300
四、余论
《论语》在西方的译介、传播、接受与研究的过程,是中国文化在西方译介、传播与接受的一个缩影。从16 世纪至今,《论语》在西方已经传播了400 多年,这期间有很多方面还未有人予以关注,本文只是尝试初略梳理其传播简史,除关注传播较为普及和充分的几个国家如美国、英国之外,也将眼光拓展到《论语》在法国、德国、俄国,甚至斯洛伐克、芬兰等国家的译介、流传与研究上。
后续的研究除了宏观方面,更应该关注微观方面:如(1)《论语》书籍是如何传入西方的,其版本如何,其中哪些人起到了关键作用;(2)各种译本依据的是哪种注疏(释),译者为什么选择了这种(些)注疏,而不是另外的注疏;(3)译本的完成是否得到了中国学者的帮助,其依赖性有多大;(4)传播中哪些因素更重要,其原因是什么等等。
尤为重要的是,以往译本所参考的《论语》文本并非均为权威注疏,而且当代的优秀研究成果并未得到及时的利用。中国学者对国内状况更为熟悉,不管是对古代还是现当代的注疏和研究成果,都容易获取和掌握。因此,中国学者可以与外国学者(包括华裔学者)合作,将《论语》及其最新研究成果推介到海外,并利用更为精当而权威的传统和现代注疏对《论语》重新进行英译,从而推出更为可读而经典的新译作。
(编辑:织言)
每日英语词汇
|
The region is struggling under the cumulative effects of concurrent and continuous crises.该地区的危机接踵而至,持续不绝,累积效应令其应接不暇。
|
文学翻译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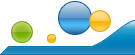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22018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2201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