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说翻译
- 剧本翻译
- 诗歌翻译
- 影视翻译
- 楹联翻译
- 广告翻译
文学翻译:游走在“漂亮”与“贞洁”之间
时间:2014/11/14 来源:豆丁网 浏览次数:2029
林少华/文
梁实秋本打算用二十年译完《莎士比亚全集》,而实际上用了三十年。译完后,同行的朋友们为他举行“庆功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讲:要译《莎士比亚全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必须不是学者,若是学者就搞研究去了;二是必须不是天才,若是天才就搞创作去了;三是必须活得相当久。“很侥幸,这三个条件我都具备。”众人听了,开怀大笑,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我当然不能同梁实秋相比,但他说的这三个条件,我也大体具备。我不是像样的学者,更不是天才,即使同作为本职工作的教书匠相比,我最为人知晓的也仍是翻译匠。
其实,即使这最为人知晓的翻译匠,也纯属歪打正着。过去有名的翻译家,如林琴南、苏曼殊、朱生豪、梁实秋、周作人、鲁迅、郭沫若、丰子恺、冰心、杨绛、傅雷、王道乾、查良铮、汝龙等人,大多出身名门望族或书香门第,自幼熟读经史,长成游学海外。故家学(国学)西学融于一炉,中文外文得心应手。翻译之余搞创作,创作之余搞翻译,或翻译创作之余做学问,往往兼翻译家、作家甚至学者于一身,如开头说的梁实秋即完全如此。而我截然有别。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出生在东北平原一个至少上五代皆躬耕田垅的“闯关东”农户之家———林姓以文功武略炳彪青史者比比皆是,但我们这一支大体无可攀附———出生不久举家迁出,随着在县供销社、乡镇机关当小干部的父亲辗转于县城和半山区村落之间。从我上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家定居在吉林省九台县土们岭公社马安山生产大队第三生产小队一个叫小北沟的仅五户人家的小山村。小山村很穷,借用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话说,穷得连乌鸦都会哭着飞走。任何人都不会想到,那样的小山沟会走出一个据说有些影响的翻译家。说白了,简直像个笑话。
回想起来,这要首先感谢我的母亲。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如果母亲不把自己稀粥碗底的饭粒拨到我的饭盒里并不时瞒着弟妹们往里放一个咸鸡蛋,我恐怕很难好好读完小学。其次要感谢我的父亲。爱看书的父亲有个书箱,里面有《三国演义》、《水浒新传》和《青春之歌》、《战斗的青春》等许多旧小说,使我从小有机会看书和接触文学。同时我还想感谢我自己———感谢自己对看书毫不含糊的痴迷。我确实喜欢看书。不喜欢说话,不喜欢和同伴嬉闹,只喜欢一个人躲在哪里静静看书。小时所有快乐的记忆、所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几乎都和书有关,现在都还好像能嗅到在煤油灯下看书摘抄漂亮句子时灯火苗突然烧着额前头发的特殊焦糊味儿。
这么着,我最喜欢上的就是语文课,成绩也最好。至于外语,毕竟那个时代的乡村小学,没有外语课,连外语这个词儿都没听说过。升上初中———因“文革”关系,只上到初一就停课了———也没学外语。由外语翻译过来的小说固然看过两三本,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个真正的人》、《贵族之家》,但没有意识到那是翻译作品。别说译者,连作者名字都不曾留意。这就是说,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完全没有外语意识和翻译意识之中度过的。由于语文和作文成绩好,对于将诗人甚至记者之类倒是偶来的职业,作家、尔模模糊糊设想过,但翻译二字从未出现在脑海,压根儿不晓得存在翻译这种活计。一如今天的孩子不晓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的是什么命。
阴差阳错,上大学学的是外语日语。不怕你笑话,学日语之前我不知晓天底下竟有日本语这个玩艺儿。以为日本人就像不知看过多少遍的《地道战》、《地雷战》里的鬼子兵一样讲半生不熟的汉语:张口“你的死啦死啦的”,闭口“你的八路的干活?八格牙路”!入学申请书上专业志愿那栏也是有的,但正值“文革”,又是贫下中农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所以那一栏填的是“一切听从党安排”。结果,不知什么缘故———至今也不知道,完全是一个谜——党安排我学了日语。假如安排我学自己喜欢和得意的中文,今天我未必成为同样有影响的作家;而若安排我学兽医,在农业基本机械化的今天,我十有八九失业或开宠物诊所给哈巴狗打绝育针。但事实是,我被安排学了日语,并成了日本文学与翻译方向的研究生导师,成了大体像那么回事、间或满世界忽悠的翻译家。不是我说漂亮话,在这个意义上,我必须感谢党,感谢党的英明安排。否则,只读到初一的山里娃娃怎么可能结缘于专门写城市题材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呢?连翻译两个字都不晓得的人怎么可能成为翻译家呢?当然,事情也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命运!或者说际遇。命运也罢际遇也罢,以中国传统文化和个人现实感受言之,恐怕都不能完全否定其中含有不可控的超越性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人的努力、人的安排。
我的翻译活动始于研究生毕业、在暨南大学任教的1982年以后。1984年是命运的安排,我为广东电视台翻译了由山口百惠和《命运》大岛茂主演的28集日本电视连续剧(赤い運命)。不瞒你说,连中文系饶芃子先生那样的名教授都说译得好。接着翻译了夏目漱石的代表作《哥儿》(坊っちゃん),最初发表于暨南大学外语系主办的《世界文艺》,刊物主编、已故英语教授张鸾玲先生赞叹“这才是小说”。1988年承蒙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日本文学专家李德纯先生推荐,我的翻译活动再次命运性地迎来一个新的起点:开始翻译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南京大学许钧教授曾对作家毕飞宇说:“一个好作家遇上一个好翻译几乎就是一场艳遇。”这句话反过来说也应该一样。 “艳遇”是什么,艳遇不仅起步顺利,整个翻其实就是命运。总之,译进程也够一帆风顺。
不过,我没有受过专门的翻译训练。既没有上过翻译专业的学位研究生班,又没有攻读有关的学术学位。而作为翻译实践,说得夸张些,可以说出手不凡。一次偶尔翻阅刚刚提及的三四十年前翻译的《哥儿》,发现那时就已达到一个今天也未必就能抵达的高度。换言之,历经三四十年漫长的岁月,我的翻译水准好像全然没有提高———这个发现让我惊讶得好半天说不出话来。那么,这是否意味翻译不必接受专业训练或者我走上翻译道路之前从未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呢?回答是否定的。就此我想说两点。一是———上面我说过了———我自小喜欢看书,喜欢文学,这培养了我的文学悟性、写作能力和修辞自觉;二是大量的文本阅读。即使在批判“白专道路”的“文革”工农兵大学生时期,我也读了多卷本《人墙》(人間の壁)、《没有太阳的街》(太陽のない街)等日本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读研三年又至少通读了漱石全集。这打磨了我的日文语感,扩大了词汇量。我教翻译课也教三四十年了,深感如今的大学生、研究生缺少的恰恰是这两点。而若无此两点,哪怕攻读十个翻译专业学位,哪怕再歪打正着也是不大可能成为翻译家尤其文学翻译家的。在此请允许我再次引用毕飞宇的话:“我可以很武断地说,现在很多翻译家外语越来越好,中文越来越差。我不懂外语,可是,有时候我能从小说自身的逻辑判断出哪里翻错了。你说,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我还是那句老话,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写作’,一个翻译家如果丧失了母语的写作能力,外语再好也没有用。”(《中华读书报》2012年6月27日)我想这段话也可以印证我所说的并非虚言,并非纯属个人自作多情。在这个意义上,我成为翻译家,既是歪打正着,又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歪打正着也罢,水到渠成也罢,反正事实上我成了翻译匠、翻译家,并且浪得一点虚名,取得一点成绩。迄今为止,以单行本计,大大小小厚厚薄薄加起来已经译了七十多本。翻译过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井上靖、三岛由纪夫和东山魁夷等多位名家之作,但翻译数量最多和时间最久的绝对是村上春树。以数量而言,译了42种,出了41种。从时间上说,自1988年开始译《挪威的森林》,已经译了二十四年。整整二十四年,二十四年之久。二十四年意味着什么呢?至少意味一个人有效工作时间的一半,意味从带一小截青春尾巴的中青年译到“鬓已星星也”的中老年。换言之,翻译之初自己犹然生龙活虎如日中天,而今已是古道瘦马日暮西风。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翻译的村上作品,二十多年来程度不同地影响了以城市青年为主体的一两代人的阅读兴趣、审美取向、生活情调以至心灵品位。可以说,翻译尤其村上作品的翻译是我大半生中所做的比较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一件具有正能量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我要感谢日本文学家村上春树天才地创造了这样的一个个有意义有价值的原始文本,感谢无数中国读者对我的译本的接受、欣赏以至批评,并且感谢世界上存在翻译这样一种文学活动形式。我想,假如没有翻译,我的人生恐怕要苍白许多瘠薄许多。毕竟,在这个教授队伍排山倒海浩浩荡荡的时代,这个正高职称不足以给自己头上带来什么光环。当然,我也可能成为多少像那么回事的学者,但以我的异常学历、知识结构和学养积淀,恐怕很难构筑自成一统的学术大厦,成就惊世骇俗的独家之言。所以,此刻我是怀着恭谨的心情谈论翻译的。
翻译这东西具体说来是相当不好说的东西,而作为译者说自己的翻译就更不好说。往好里说吧,人家会说你老王头卖瓜自卖自夸,不懂谦虚是美德;往糟里说吧,自己又不甘心,也未必公平。总之左右为难。 但如果不说自己,只是泛泛而论,又可能十分好说。比如董桥,最近偶然翻阅他的一本名叫《乡愁的理念》的小书,里面谈到翻译,谈得极俏皮:“下等译匠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给原文压得扁扁的,只好忍气吞声;高等译手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跟原文平起平坐,谈情说爱,毫无顾忌。”还有一段说得颇有色情之嫌,我都不好意思引用,他是这么说的:“好的翻译,是男欢女爱,如鱼得水,一拍即合。读起来像中文,像人话,顺极了。坏的翻译,是同床异梦,人家无动于衷,自己欲罢不能,最后只好‘进行强奸’,硬来硬要,乱射一通,读起来像鬼话,既亵渎了外文也亵渎了中文。”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意大利也有异曲同工的说法:“翻译如女人,漂亮的不贞洁,贞洁的不漂亮”。言外之意,理想的翻译就是要既贞洁又漂亮。以上面董桥的话说,就是要跟原文谈情说爱平起平坐,进而男欢女爱如鱼得水。如果换成钱锺书,只一个字:化!他说:“文学翻译的高标准是最‘化’。”古今中外,关于翻译的言说不可谓不多,但相比之下,我还是最欣赏钱老先生这个“化”字。即使严复的“信、达、雅”三个字,也可用此“化”字化而为一。而翻译的所有问题,依我愚见,也都出在这个“化”字上面,就是说没有“化”好———或“忍气吞声”,或“同床异梦”,或贞洁与漂亮非此即彼、两相叛离。
与此同时,关于翻译的所有争论也都几乎离不开这个“化”字。如贞洁与漂亮、意译与直译、神似与形似、归化与异化、等值与超越、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语体忠实与审美忠实等,不一而足。
“化”得最好的,英文汉译方面我虽然不太熟悉,但至少王佐良先生译的培根读书名言算是其一:“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英汉之间,妙而化之,天衣无缝。 汉译法国文学方面,翻译家罗新璋先生最服傅雷,他举傅译《约翰·克里斯朵夫》开头一句为例:“le grondement du fleuve monte derriè re lamaison”直译为“大江的轰隆轰隆声,从屋子后面升上来”;而傅雷译成:“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化人为己,水乳交融,斐然而成名译。日本文学翻译方面“化”得最好的,窃以为是丰子恺先生译的《源氏物语》,鬼斧神工,出神入化,信手拈来,绝尘而去。读之可知译事之难,可叹译笔之工,可生敬畏之情。词意或有不逮,理解或有偏差,但在整体审美传达上迄今无人可比。不料随手翻看《书城》(2009年10月号余斌文《知堂“酷评”》),发现周作人对丰译的评价极其尖刻,谓丰子恺译文“喜用俗恶成语”、“只是很漂亮滥用成语,不顾与原文空气相合与否……其实此译根本不可用”,还说“丰氏源氏译稿,是茶店说书,似尚不明白源氏是什么书也”,一句话,只漂亮不贞洁,“俗恶”!那么他本人译的就既漂亮又贞洁了么?未必。贞洁或许贞洁,可惜贞洁得近乎“涩”,整体审美效果明显在丰译之下。说句不恭的话吧,周作人的夫人是日本人,按理,他搞翻译应该“男欢女爱如鱼得水”才是,可他却好像“给原文压得扁扁的”,大气不敢出。这固然同他创作中标举的“简单味”、“涩味”之文章境界有关,但同时也和他采取的异化这一翻译策略有关,用当下较为流行的说法,就是“去中国化”,即主要对日文原著负责。而他之所以酷评丰译为“俗恶”,自是因为———在他看来———丰译的“去日本化”。
上面所以说这许多,也是因为同我的翻译理念和翻译策略有关。我的翻译理念———如果说我有这劳什子的话———主要是对中国、中国读者负责,即要首先确认自己的翻译能给中国读者、中国文化以至中国社会带来什么。 借用周作人的兄长鲁迅的话,就是要看自己像普罗米修斯那样为中国窃得的是火种还是别的什么。这样,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势必与周作人相反,而要尽可能消除“涩味”,也就是消除日译汉特有的翻译腔(“和臭”)。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去日本化”也未尝不可。换言之,就是想方设法琢磨找一个既贞洁又漂亮的“女人”,这也是天底下所有男人尤其男翻译家一生的梦想。不是吗?有哪个男人存心想找一个只漂亮不贞洁或只贞洁不漂亮的女人呢?那么,之于我的既贞洁又漂亮的“女人”到底找到了没有呢?我以为大体找到了,至少在贞洁与漂亮之间找到了一个接合点。我一再主张的“审美忠实”也就是这个意思。我以为,就文学翻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审美忠实。
说到这里,请容我说一下我的翻译观,即我所大体认同的关于翻译的言说或观点,当然也多少包括我个人的体悟。我倾向于认为,文学翻译必须是文学———翻译文学。大凡文学都是艺术———语言艺术。大凡艺术都需要创造性,因此文学翻译也需要创造性。但文学翻译毕竟是翻译而非原创,因此准确说来,文学翻译属于再创造的艺术。以严复的“信达雅”言之:“信”,侧重于内容(内容忠实);“达”,侧重于行文(行文忠实);“雅”,侧重于艺术境界(艺术忠实)。“信、达”需要知性判断,“雅”则更需要审美判断。审美判断要求译者具有艺术悟性、文学悟性。但不可否认,事实上并非每个译者都具有相应的悟性。与此相关,翻译或可大体分为三种:工匠型翻译,学者型翻译,才子型翻译。工匠型亦步亦趋,貌似“忠实”;学者型中规中矩,刻意求工;才子型惟妙惟肖,意在传神。学者型如朱光潜、季羡林,才子型如丰子恺、王道乾,二者兼具型如傅雷、梁实秋。至于工匠型翻译,当下比比皆是,举不胜举,也不敢举。严格说来,那已不是文学翻译,更不是翻译文学。 翻译匠和翻译家的区别在于,前者传达语法、意思和故事,后者再现表情、心跳或审美愉悦。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文学翻译最重要的就是审美忠实。就文学翻译中形式(语言表象)层、风格(文体)层和审美(品格)层这三个层面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审美层。即使“叛逆”,也要形式层的叛逆服从风格层,风格层的叛逆服从审美层,而审美层是不可叛逆的文学翻译之重。《达·芬奇密码》的译者朱振武教授在2011年第6期《外国文艺》发表文章,也一再强调审美的重要:“文学翻译是艺术化的翻译,是译者对原作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的审美把握……文学翻译不是词句的形式对应,而是语言信息与美感信息的整体吸纳与再造。”
不无遗憾的是,审美视角的阙如正是目前文学翻译实践、文学翻译批评的盲点所在。窃以为,随着国际交流的频繁和懂外语人数的迅速增加,当下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主要问题,较之准确性,恐怕更在于文学审美的缺位。用罗新璋先生的话说,翻译过来的不是文学,而是一堆堆文字。以致“读起来味同嚼蜡,给读者充分的机会去体验阅读的艰辛,而不是享受阅读的愉悦”(虞建华语,见《外国文艺》2010年第4期)。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原作本身是否味同嚼蜡?如果不是,那么译者标榜的忠实或准确性又体现在哪里呢?事情十分清楚,那才是致命的不忠实、不准确,纵然语法、词汇、句式等形式层面贴得很紧甚至无懈可击。换言之,无论有多少理由,翻译文学作品都不该丢掉审美、丢掉审美忠实。如果丢掉审美忠实,其它所有忠实都不过是“伪忠实”,不过是徒有其表的蜡人罢了,而蜡人纵使再漂亮也不可能走进人的心里。
接下来谈一下“美化”问题。无论国内国外,对拙译的批评和误解主要集中在这里。说得通俗些,人家村上原本长相平平,是我给打扮漂亮了,打扮得油头粉面花枝招展。换言之,我笔下的美人是不忠的美人、不贞洁的美人,而我却固执地认为自己找到的是既贞洁又漂亮的。 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想这里边有这样两个问题。首先,总体上我并不认为存在“美化”问题,至少主观上没有这样的意图。那么客观上为什么给一些读者甚至学者那样的感觉呢?细想之下,起因大概有二。一是同我对村上文学的定位有关。我认为村上文学并非一味以口语体和可读性为主的通俗文学(大众文学),而是有知性追求和审美志向的严肃文学(纯文学),因此在翻译当中怀有一种“精品”意识,一丝不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二是同一个人的文学才情有关。这也没有什么可谦虚的,搞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一定要有相应的才情,没有才情肯定搞不好。作为我,除了翻译还多少搞一点创作。可以说,自己惟一的强项和乐趣就是舞文弄墨。舞弄得意之时,颇有“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之感。翻译过程中每觉如有神助,文思泉涌,一泻而下。所以,即使多少译得“美”些,那也无非是一点点文学才情的自然流露,而非刻意“美化”所致。
再退一步说,即使“美化”又有什么不好?许渊冲先生写了一本书,叫《文学翻译六十年》,其中有一篇文章就叫《美化之艺术》,强调文学翻译就是要在不失真的情况下求美,就是要化原文之美为译文之美。换个说法,就是要在保持贞洁的前提下追求最大限度的漂亮,以满足读者的审美期待,使之读起来产生审美愉悦。无须说,最理想的是等化翻译。然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百分之百的等化翻译是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翻译永远是向原作文体、原作境界无限逼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稍一偏离就涉及或美化或淡化甚至丑化的问题,几乎人人涉嫌。既然如此,优化、美化总比淡化、丑化要好吧?总不能说翻译得越枯燥无味越好嘛!毕竟原作不至于枯燥无味。 况且,文学、文学翻译既是语言艺术,那么总要字斟句酌反复提炼,总要高于现实生活中的语言,否则还要文学作品干什么呢?
等化译法和“美化”译法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翻译学中常说的“异化”和“归化”(同化)的翻译策略问题,这其实也是文体的翻译和翻译的文体或者原作者文体和译者文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最好的翻译当然是百分之百等同于原作者文体的翻译。问题是,翻译既是再创造的艺术,就必然有译者个性、译者风格即译者文体介入其间。关于这点,兼搞翻译的村上春树本人也持同一观点。他说:“我的小说有一种类似翻译文体的蜕变(脱構築)或其偷梁换柱的地方,翻译中也会出现”。并说他翻译卡佛时“尽管千方百计使之成为标准翻译,但我的卡佛在结果上还是带有我的倾向性”。他还这样说过:“我想,出色的翻译首先需要的恐怕是语言能力,但同样需要的还有———尤其文学作品———充满个人偏见的爱。说得极端些,只要有了这点,其它概不需要。说起我对自己这作品的翻译的首要希求,恰恰就是这点。”这里所说的“充满偏见的爱”,完全可以理解为并非“标准翻译”的个人倾向性。不可否认,我翻译的村上也难免带有我的文体倾向,只能是“林家铺子”的村上而不是王家铺子张家铺子的村上。换言之,作为纯净水文体的翻译是没有的,翻译只能是原作者文体和译者文体,或者文体的翻译和翻译的文体相妥协相融合的产物。这既是文学翻译的无奈之处,又是文学翻译的妙趣和价值所在———原作因此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也正因为村上文学在中国的第二次生命是中文赋予的,所以它已不再是纯粹外国文学意义上的日本文学,而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道理很简单,以中文出现的村上文学无论翻译得多么精彩,也决不可能在日本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而只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寻找它的位置。因而我这个译介者的名字只能出现在中国文学史而绝无可能载入日本文学史册。 就这点而言,对中译村上作品的全面评价,主要不是看它对日文给中负什么责任,而应该看它给中国读者、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以至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这也是我翻译村上的根本出发点和么—着陆点。
在结束之前,请允许我谈几句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藤井省三先生。这是因为,拙译的“美化”问题在国外最先提出的是藤井先生并直接影响到国内。他在《村上春树心底的中国》(「村上春樹のなかの中国」,朝日新闻社2007年)中以《挪威的森林》里玲子弹吉他那一段译文为例,批评拙译的“审美忠实”显得“浓妆艳抹”(厚化粧),进而概括性批评拙译是“汉语民族主义”(中国語ナショナリズム)、“不无过剩的文化民族主义”(い。ささか過剰な文化的ナショナリズム)态度之决绝,手法之多变,用词之苛薄,明显超过了公允而理性的学术批评范畴,而就个人关系来说我们又未尝不可以说是朋友。这就留下了一个问号: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对此我断断续续想了三四年,最近终于茅塞顿开:根本原因就在于在他眼里拙译是“去日本化”的,也就是说,汉语在这里成了主导性优势语言,而他大约是希望拙译“给原文压得扁扁的”。这样,所谓“民族主义”云云也就不难理解了。但这样一来,就留下另一个问号:究竟谁是民族主义?
其实大部分人都有民族主义倾向,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把民族主义强行带入非关民族主义的翻译以至学术批评。一般说来,文学翻译并非政治活动,而是艺术活动、审美活动。因此,审美忠实始终是我明确的指向和追求。既美且忠,既贞洁又漂亮,行吟于二者之间而逐渐归于“化境”———“化”是中国艺术最高境界,雕塑也罢绘画也罢创作也罢翻译也罢。翻译之妙,惟“化”而已。也只有这样,贞洁和漂亮才有可能兼而得之。
梁实秋本打算用二十年译完《莎士比亚全集》,而实际上用了三十年。译完后,同行的朋友们为他举行“庆功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讲:要译《莎士比亚全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必须不是学者,若是学者就搞研究去了;二是必须不是天才,若是天才就搞创作去了;三是必须活得相当久。“很侥幸,这三个条件我都具备。”众人听了,开怀大笑,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我当然不能同梁实秋相比,但他说的这三个条件,我也大体具备。我不是像样的学者,更不是天才,即使同作为本职工作的教书匠相比,我最为人知晓的也仍是翻译匠。
其实,即使这最为人知晓的翻译匠,也纯属歪打正着。过去有名的翻译家,如林琴南、苏曼殊、朱生豪、梁实秋、周作人、鲁迅、郭沫若、丰子恺、冰心、杨绛、傅雷、王道乾、查良铮、汝龙等人,大多出身名门望族或书香门第,自幼熟读经史,长成游学海外。故家学(国学)西学融于一炉,中文外文得心应手。翻译之余搞创作,创作之余搞翻译,或翻译创作之余做学问,往往兼翻译家、作家甚至学者于一身,如开头说的梁实秋即完全如此。而我截然有别。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出生在东北平原一个至少上五代皆躬耕田垅的“闯关东”农户之家———林姓以文功武略炳彪青史者比比皆是,但我们这一支大体无可攀附———出生不久举家迁出,随着在县供销社、乡镇机关当小干部的父亲辗转于县城和半山区村落之间。从我上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家定居在吉林省九台县土们岭公社马安山生产大队第三生产小队一个叫小北沟的仅五户人家的小山村。小山村很穷,借用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话说,穷得连乌鸦都会哭着飞走。任何人都不会想到,那样的小山沟会走出一个据说有些影响的翻译家。说白了,简直像个笑话。
回想起来,这要首先感谢我的母亲。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如果母亲不把自己稀粥碗底的饭粒拨到我的饭盒里并不时瞒着弟妹们往里放一个咸鸡蛋,我恐怕很难好好读完小学。其次要感谢我的父亲。爱看书的父亲有个书箱,里面有《三国演义》、《水浒新传》和《青春之歌》、《战斗的青春》等许多旧小说,使我从小有机会看书和接触文学。同时我还想感谢我自己———感谢自己对看书毫不含糊的痴迷。我确实喜欢看书。不喜欢说话,不喜欢和同伴嬉闹,只喜欢一个人躲在哪里静静看书。小时所有快乐的记忆、所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几乎都和书有关,现在都还好像能嗅到在煤油灯下看书摘抄漂亮句子时灯火苗突然烧着额前头发的特殊焦糊味儿。
这么着,我最喜欢上的就是语文课,成绩也最好。至于外语,毕竟那个时代的乡村小学,没有外语课,连外语这个词儿都没听说过。升上初中———因“文革”关系,只上到初一就停课了———也没学外语。由外语翻译过来的小说固然看过两三本,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个真正的人》、《贵族之家》,但没有意识到那是翻译作品。别说译者,连作者名字都不曾留意。这就是说,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完全没有外语意识和翻译意识之中度过的。由于语文和作文成绩好,对于将诗人甚至记者之类倒是偶来的职业,作家、尔模模糊糊设想过,但翻译二字从未出现在脑海,压根儿不晓得存在翻译这种活计。一如今天的孩子不晓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的是什么命。
阴差阳错,上大学学的是外语日语。不怕你笑话,学日语之前我不知晓天底下竟有日本语这个玩艺儿。以为日本人就像不知看过多少遍的《地道战》、《地雷战》里的鬼子兵一样讲半生不熟的汉语:张口“你的死啦死啦的”,闭口“你的八路的干活?八格牙路”!入学申请书上专业志愿那栏也是有的,但正值“文革”,又是贫下中农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所以那一栏填的是“一切听从党安排”。结果,不知什么缘故———至今也不知道,完全是一个谜——党安排我学了日语。假如安排我学自己喜欢和得意的中文,今天我未必成为同样有影响的作家;而若安排我学兽医,在农业基本机械化的今天,我十有八九失业或开宠物诊所给哈巴狗打绝育针。但事实是,我被安排学了日语,并成了日本文学与翻译方向的研究生导师,成了大体像那么回事、间或满世界忽悠的翻译家。不是我说漂亮话,在这个意义上,我必须感谢党,感谢党的英明安排。否则,只读到初一的山里娃娃怎么可能结缘于专门写城市题材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呢?连翻译两个字都不晓得的人怎么可能成为翻译家呢?当然,事情也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命运!或者说际遇。命运也罢际遇也罢,以中国传统文化和个人现实感受言之,恐怕都不能完全否定其中含有不可控的超越性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人的努力、人的安排。
我的翻译活动始于研究生毕业、在暨南大学任教的1982年以后。1984年是命运的安排,我为广东电视台翻译了由山口百惠和《命运》大岛茂主演的28集日本电视连续剧(赤い運命)。不瞒你说,连中文系饶芃子先生那样的名教授都说译得好。接着翻译了夏目漱石的代表作《哥儿》(坊っちゃん),最初发表于暨南大学外语系主办的《世界文艺》,刊物主编、已故英语教授张鸾玲先生赞叹“这才是小说”。1988年承蒙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日本文学专家李德纯先生推荐,我的翻译活动再次命运性地迎来一个新的起点:开始翻译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南京大学许钧教授曾对作家毕飞宇说:“一个好作家遇上一个好翻译几乎就是一场艳遇。”这句话反过来说也应该一样。 “艳遇”是什么,艳遇不仅起步顺利,整个翻其实就是命运。总之,译进程也够一帆风顺。
不过,我没有受过专门的翻译训练。既没有上过翻译专业的学位研究生班,又没有攻读有关的学术学位。而作为翻译实践,说得夸张些,可以说出手不凡。一次偶尔翻阅刚刚提及的三四十年前翻译的《哥儿》,发现那时就已达到一个今天也未必就能抵达的高度。换言之,历经三四十年漫长的岁月,我的翻译水准好像全然没有提高———这个发现让我惊讶得好半天说不出话来。那么,这是否意味翻译不必接受专业训练或者我走上翻译道路之前从未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呢?回答是否定的。就此我想说两点。一是———上面我说过了———我自小喜欢看书,喜欢文学,这培养了我的文学悟性、写作能力和修辞自觉;二是大量的文本阅读。即使在批判“白专道路”的“文革”工农兵大学生时期,我也读了多卷本《人墙》(人間の壁)、《没有太阳的街》(太陽のない街)等日本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读研三年又至少通读了漱石全集。这打磨了我的日文语感,扩大了词汇量。我教翻译课也教三四十年了,深感如今的大学生、研究生缺少的恰恰是这两点。而若无此两点,哪怕攻读十个翻译专业学位,哪怕再歪打正着也是不大可能成为翻译家尤其文学翻译家的。在此请允许我再次引用毕飞宇的话:“我可以很武断地说,现在很多翻译家外语越来越好,中文越来越差。我不懂外语,可是,有时候我能从小说自身的逻辑判断出哪里翻错了。你说,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我还是那句老话,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写作’,一个翻译家如果丧失了母语的写作能力,外语再好也没有用。”(《中华读书报》2012年6月27日)我想这段话也可以印证我所说的并非虚言,并非纯属个人自作多情。在这个意义上,我成为翻译家,既是歪打正着,又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歪打正着也罢,水到渠成也罢,反正事实上我成了翻译匠、翻译家,并且浪得一点虚名,取得一点成绩。迄今为止,以单行本计,大大小小厚厚薄薄加起来已经译了七十多本。翻译过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井上靖、三岛由纪夫和东山魁夷等多位名家之作,但翻译数量最多和时间最久的绝对是村上春树。以数量而言,译了42种,出了41种。从时间上说,自1988年开始译《挪威的森林》,已经译了二十四年。整整二十四年,二十四年之久。二十四年意味着什么呢?至少意味一个人有效工作时间的一半,意味从带一小截青春尾巴的中青年译到“鬓已星星也”的中老年。换言之,翻译之初自己犹然生龙活虎如日中天,而今已是古道瘦马日暮西风。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翻译的村上作品,二十多年来程度不同地影响了以城市青年为主体的一两代人的阅读兴趣、审美取向、生活情调以至心灵品位。可以说,翻译尤其村上作品的翻译是我大半生中所做的比较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一件具有正能量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我要感谢日本文学家村上春树天才地创造了这样的一个个有意义有价值的原始文本,感谢无数中国读者对我的译本的接受、欣赏以至批评,并且感谢世界上存在翻译这样一种文学活动形式。我想,假如没有翻译,我的人生恐怕要苍白许多瘠薄许多。毕竟,在这个教授队伍排山倒海浩浩荡荡的时代,这个正高职称不足以给自己头上带来什么光环。当然,我也可能成为多少像那么回事的学者,但以我的异常学历、知识结构和学养积淀,恐怕很难构筑自成一统的学术大厦,成就惊世骇俗的独家之言。所以,此刻我是怀着恭谨的心情谈论翻译的。
翻译这东西具体说来是相当不好说的东西,而作为译者说自己的翻译就更不好说。往好里说吧,人家会说你老王头卖瓜自卖自夸,不懂谦虚是美德;往糟里说吧,自己又不甘心,也未必公平。总之左右为难。 但如果不说自己,只是泛泛而论,又可能十分好说。比如董桥,最近偶然翻阅他的一本名叫《乡愁的理念》的小书,里面谈到翻译,谈得极俏皮:“下等译匠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给原文压得扁扁的,只好忍气吞声;高等译手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跟原文平起平坐,谈情说爱,毫无顾忌。”还有一段说得颇有色情之嫌,我都不好意思引用,他是这么说的:“好的翻译,是男欢女爱,如鱼得水,一拍即合。读起来像中文,像人话,顺极了。坏的翻译,是同床异梦,人家无动于衷,自己欲罢不能,最后只好‘进行强奸’,硬来硬要,乱射一通,读起来像鬼话,既亵渎了外文也亵渎了中文。”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意大利也有异曲同工的说法:“翻译如女人,漂亮的不贞洁,贞洁的不漂亮”。言外之意,理想的翻译就是要既贞洁又漂亮。以上面董桥的话说,就是要跟原文谈情说爱平起平坐,进而男欢女爱如鱼得水。如果换成钱锺书,只一个字:化!他说:“文学翻译的高标准是最‘化’。”古今中外,关于翻译的言说不可谓不多,但相比之下,我还是最欣赏钱老先生这个“化”字。即使严复的“信、达、雅”三个字,也可用此“化”字化而为一。而翻译的所有问题,依我愚见,也都出在这个“化”字上面,就是说没有“化”好———或“忍气吞声”,或“同床异梦”,或贞洁与漂亮非此即彼、两相叛离。
与此同时,关于翻译的所有争论也都几乎离不开这个“化”字。如贞洁与漂亮、意译与直译、神似与形似、归化与异化、等值与超越、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语体忠实与审美忠实等,不一而足。
“化”得最好的,英文汉译方面我虽然不太熟悉,但至少王佐良先生译的培根读书名言算是其一:“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英汉之间,妙而化之,天衣无缝。 汉译法国文学方面,翻译家罗新璋先生最服傅雷,他举傅译《约翰·克里斯朵夫》开头一句为例:“le grondement du fleuve monte derriè re lamaison”直译为“大江的轰隆轰隆声,从屋子后面升上来”;而傅雷译成:“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化人为己,水乳交融,斐然而成名译。日本文学翻译方面“化”得最好的,窃以为是丰子恺先生译的《源氏物语》,鬼斧神工,出神入化,信手拈来,绝尘而去。读之可知译事之难,可叹译笔之工,可生敬畏之情。词意或有不逮,理解或有偏差,但在整体审美传达上迄今无人可比。不料随手翻看《书城》(2009年10月号余斌文《知堂“酷评”》),发现周作人对丰译的评价极其尖刻,谓丰子恺译文“喜用俗恶成语”、“只是很漂亮滥用成语,不顾与原文空气相合与否……其实此译根本不可用”,还说“丰氏源氏译稿,是茶店说书,似尚不明白源氏是什么书也”,一句话,只漂亮不贞洁,“俗恶”!那么他本人译的就既漂亮又贞洁了么?未必。贞洁或许贞洁,可惜贞洁得近乎“涩”,整体审美效果明显在丰译之下。说句不恭的话吧,周作人的夫人是日本人,按理,他搞翻译应该“男欢女爱如鱼得水”才是,可他却好像“给原文压得扁扁的”,大气不敢出。这固然同他创作中标举的“简单味”、“涩味”之文章境界有关,但同时也和他采取的异化这一翻译策略有关,用当下较为流行的说法,就是“去中国化”,即主要对日文原著负责。而他之所以酷评丰译为“俗恶”,自是因为———在他看来———丰译的“去日本化”。
上面所以说这许多,也是因为同我的翻译理念和翻译策略有关。我的翻译理念———如果说我有这劳什子的话———主要是对中国、中国读者负责,即要首先确认自己的翻译能给中国读者、中国文化以至中国社会带来什么。 借用周作人的兄长鲁迅的话,就是要看自己像普罗米修斯那样为中国窃得的是火种还是别的什么。这样,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势必与周作人相反,而要尽可能消除“涩味”,也就是消除日译汉特有的翻译腔(“和臭”)。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去日本化”也未尝不可。换言之,就是想方设法琢磨找一个既贞洁又漂亮的“女人”,这也是天底下所有男人尤其男翻译家一生的梦想。不是吗?有哪个男人存心想找一个只漂亮不贞洁或只贞洁不漂亮的女人呢?那么,之于我的既贞洁又漂亮的“女人”到底找到了没有呢?我以为大体找到了,至少在贞洁与漂亮之间找到了一个接合点。我一再主张的“审美忠实”也就是这个意思。我以为,就文学翻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审美忠实。
说到这里,请容我说一下我的翻译观,即我所大体认同的关于翻译的言说或观点,当然也多少包括我个人的体悟。我倾向于认为,文学翻译必须是文学———翻译文学。大凡文学都是艺术———语言艺术。大凡艺术都需要创造性,因此文学翻译也需要创造性。但文学翻译毕竟是翻译而非原创,因此准确说来,文学翻译属于再创造的艺术。以严复的“信达雅”言之:“信”,侧重于内容(内容忠实);“达”,侧重于行文(行文忠实);“雅”,侧重于艺术境界(艺术忠实)。“信、达”需要知性判断,“雅”则更需要审美判断。审美判断要求译者具有艺术悟性、文学悟性。但不可否认,事实上并非每个译者都具有相应的悟性。与此相关,翻译或可大体分为三种:工匠型翻译,学者型翻译,才子型翻译。工匠型亦步亦趋,貌似“忠实”;学者型中规中矩,刻意求工;才子型惟妙惟肖,意在传神。学者型如朱光潜、季羡林,才子型如丰子恺、王道乾,二者兼具型如傅雷、梁实秋。至于工匠型翻译,当下比比皆是,举不胜举,也不敢举。严格说来,那已不是文学翻译,更不是翻译文学。 翻译匠和翻译家的区别在于,前者传达语法、意思和故事,后者再现表情、心跳或审美愉悦。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文学翻译最重要的就是审美忠实。就文学翻译中形式(语言表象)层、风格(文体)层和审美(品格)层这三个层面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审美层。即使“叛逆”,也要形式层的叛逆服从风格层,风格层的叛逆服从审美层,而审美层是不可叛逆的文学翻译之重。《达·芬奇密码》的译者朱振武教授在2011年第6期《外国文艺》发表文章,也一再强调审美的重要:“文学翻译是艺术化的翻译,是译者对原作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的审美把握……文学翻译不是词句的形式对应,而是语言信息与美感信息的整体吸纳与再造。”
不无遗憾的是,审美视角的阙如正是目前文学翻译实践、文学翻译批评的盲点所在。窃以为,随着国际交流的频繁和懂外语人数的迅速增加,当下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主要问题,较之准确性,恐怕更在于文学审美的缺位。用罗新璋先生的话说,翻译过来的不是文学,而是一堆堆文字。以致“读起来味同嚼蜡,给读者充分的机会去体验阅读的艰辛,而不是享受阅读的愉悦”(虞建华语,见《外国文艺》2010年第4期)。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原作本身是否味同嚼蜡?如果不是,那么译者标榜的忠实或准确性又体现在哪里呢?事情十分清楚,那才是致命的不忠实、不准确,纵然语法、词汇、句式等形式层面贴得很紧甚至无懈可击。换言之,无论有多少理由,翻译文学作品都不该丢掉审美、丢掉审美忠实。如果丢掉审美忠实,其它所有忠实都不过是“伪忠实”,不过是徒有其表的蜡人罢了,而蜡人纵使再漂亮也不可能走进人的心里。
接下来谈一下“美化”问题。无论国内国外,对拙译的批评和误解主要集中在这里。说得通俗些,人家村上原本长相平平,是我给打扮漂亮了,打扮得油头粉面花枝招展。换言之,我笔下的美人是不忠的美人、不贞洁的美人,而我却固执地认为自己找到的是既贞洁又漂亮的。 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想这里边有这样两个问题。首先,总体上我并不认为存在“美化”问题,至少主观上没有这样的意图。那么客观上为什么给一些读者甚至学者那样的感觉呢?细想之下,起因大概有二。一是同我对村上文学的定位有关。我认为村上文学并非一味以口语体和可读性为主的通俗文学(大众文学),而是有知性追求和审美志向的严肃文学(纯文学),因此在翻译当中怀有一种“精品”意识,一丝不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二是同一个人的文学才情有关。这也没有什么可谦虚的,搞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一定要有相应的才情,没有才情肯定搞不好。作为我,除了翻译还多少搞一点创作。可以说,自己惟一的强项和乐趣就是舞文弄墨。舞弄得意之时,颇有“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之感。翻译过程中每觉如有神助,文思泉涌,一泻而下。所以,即使多少译得“美”些,那也无非是一点点文学才情的自然流露,而非刻意“美化”所致。
再退一步说,即使“美化”又有什么不好?许渊冲先生写了一本书,叫《文学翻译六十年》,其中有一篇文章就叫《美化之艺术》,强调文学翻译就是要在不失真的情况下求美,就是要化原文之美为译文之美。换个说法,就是要在保持贞洁的前提下追求最大限度的漂亮,以满足读者的审美期待,使之读起来产生审美愉悦。无须说,最理想的是等化翻译。然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百分之百的等化翻译是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翻译永远是向原作文体、原作境界无限逼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稍一偏离就涉及或美化或淡化甚至丑化的问题,几乎人人涉嫌。既然如此,优化、美化总比淡化、丑化要好吧?总不能说翻译得越枯燥无味越好嘛!毕竟原作不至于枯燥无味。 况且,文学、文学翻译既是语言艺术,那么总要字斟句酌反复提炼,总要高于现实生活中的语言,否则还要文学作品干什么呢?
等化译法和“美化”译法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翻译学中常说的“异化”和“归化”(同化)的翻译策略问题,这其实也是文体的翻译和翻译的文体或者原作者文体和译者文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最好的翻译当然是百分之百等同于原作者文体的翻译。问题是,翻译既是再创造的艺术,就必然有译者个性、译者风格即译者文体介入其间。关于这点,兼搞翻译的村上春树本人也持同一观点。他说:“我的小说有一种类似翻译文体的蜕变(脱構築)或其偷梁换柱的地方,翻译中也会出现”。并说他翻译卡佛时“尽管千方百计使之成为标准翻译,但我的卡佛在结果上还是带有我的倾向性”。他还这样说过:“我想,出色的翻译首先需要的恐怕是语言能力,但同样需要的还有———尤其文学作品———充满个人偏见的爱。说得极端些,只要有了这点,其它概不需要。说起我对自己这作品的翻译的首要希求,恰恰就是这点。”这里所说的“充满偏见的爱”,完全可以理解为并非“标准翻译”的个人倾向性。不可否认,我翻译的村上也难免带有我的文体倾向,只能是“林家铺子”的村上而不是王家铺子张家铺子的村上。换言之,作为纯净水文体的翻译是没有的,翻译只能是原作者文体和译者文体,或者文体的翻译和翻译的文体相妥协相融合的产物。这既是文学翻译的无奈之处,又是文学翻译的妙趣和价值所在———原作因此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也正因为村上文学在中国的第二次生命是中文赋予的,所以它已不再是纯粹外国文学意义上的日本文学,而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道理很简单,以中文出现的村上文学无论翻译得多么精彩,也决不可能在日本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而只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寻找它的位置。因而我这个译介者的名字只能出现在中国文学史而绝无可能载入日本文学史册。 就这点而言,对中译村上作品的全面评价,主要不是看它对日文给中负什么责任,而应该看它给中国读者、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以至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这也是我翻译村上的根本出发点和么—着陆点。
在结束之前,请允许我谈几句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藤井省三先生。这是因为,拙译的“美化”问题在国外最先提出的是藤井先生并直接影响到国内。他在《村上春树心底的中国》(「村上春樹のなかの中国」,朝日新闻社2007年)中以《挪威的森林》里玲子弹吉他那一段译文为例,批评拙译的“审美忠实”显得“浓妆艳抹”(厚化粧),进而概括性批评拙译是“汉语民族主义”(中国語ナショナリズム)、“不无过剩的文化民族主义”(い。ささか過剰な文化的ナショナリズム)态度之决绝,手法之多变,用词之苛薄,明显超过了公允而理性的学术批评范畴,而就个人关系来说我们又未尝不可以说是朋友。这就留下了一个问号: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对此我断断续续想了三四年,最近终于茅塞顿开:根本原因就在于在他眼里拙译是“去日本化”的,也就是说,汉语在这里成了主导性优势语言,而他大约是希望拙译“给原文压得扁扁的”。这样,所谓“民族主义”云云也就不难理解了。但这样一来,就留下另一个问号:究竟谁是民族主义?
其实大部分人都有民族主义倾向,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把民族主义强行带入非关民族主义的翻译以至学术批评。一般说来,文学翻译并非政治活动,而是艺术活动、审美活动。因此,审美忠实始终是我明确的指向和追求。既美且忠,既贞洁又漂亮,行吟于二者之间而逐渐归于“化境”———“化”是中国艺术最高境界,雕塑也罢绘画也罢创作也罢翻译也罢。翻译之妙,惟“化”而已。也只有这样,贞洁和漂亮才有可能兼而得之。
(编辑:T-win)
每日英语词汇
|
The region is struggling under the cumulative effects of concurrent and continuous crises.该地区的危机接踵而至,持续不绝,累积效应令其应接不暇。
|
文学翻译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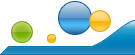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22018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22018号